| 中國新聞社主辦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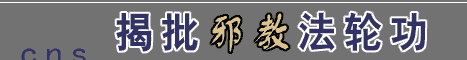 |
           |
| |
世界七大邪教(一):轟然倒塌的“人民圣殿” 2001年3月30日 13:20
1978年11月18日,從獨立未滿十年的南美小國圭亞那的熱帶叢林深處,傳出了一條令全世界震驚的慘訊:美國“人民圣殿教”900多名信徒在其教主吉姆·瓊斯的帶領下集體“自殺”!美國政府、圭亞那政府表示遺憾和不安。 一時可忙壞了各大新聞媒體。記者們紛紛趕往圭亞那、趕往美國,編輯們更是趕緊修改正要發稿的當年重大新聞的排行榜。 不用說,最忙最亂的當然是美國。所有人心頭都蒙上了一層重重的陰影,人們驚愕不解,人們焦慮困惑。 來自圭亞那的消息說,警方的飛機第二天清晨飛臨出事地點,從高空看下去,地上好像停放著一大片五顏六色的小汽車,飛近才看清那都是穿著各色T恤衫或運動服的尸身。走進營地,尸體密密麻麻,遍地都是,其狀慘不忍睹。在一個箱子里找到803本美國護照、一疊老年教徒填寫的社會福利登記證,以及,100多萬美元現鈔……現場沒有打斗痕跡,除了教主瓊斯以外沒見有槍傷,死者的面部表情大多為痙攣狀…… 初步清點后,圭亞那警方宣布死者共373人;接著又增加到409人,并分析認為其他400余人可能已逃往別處。 情況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搞清的。美國政府派出專家組緊急前往圭亞那,國內每一位居民都不安地等待著調查結果。不久,美國空軍上尉約翰·穆斯卡特里告訴記者們:圭亞那人在計數上有嚴重遺漏,死亡人數至少為780人。 即使知道生還的可能已極其之小,教徒的親友們仍不放棄最后一線希望。與此同時,美國空軍飛行員也堅持在出事地點附近不斷地進行超低空飛行,尋找幸存者。飛行員通過擴音器反復喊: “出來吧,現在安全了。” “出來吧,政府派我們來營救你了。” “你們在哪兒……” 可是,回答他們的始終是一片死寂。 最后,清理工作結束了,死亡者人數上升到了914人。 整個事件只有5名幸存者,三人在臨出事前被派出執行任務,另外兩人是年過八旬的病弱老者,他們因行動不便而沒有參加集體行動。 到了第二年3月,美國《新聞周刊》又發表一篇報道,題曰《瓊斯敦的另一個受害者》,摘要如下: 邁克爾·普羅克斯是人民圣殿教去年年底在圭亞那誘使900人進行集體自殺事件的一個幸存者。但是這個悲劇最后還是饒不了他。上星期,他在加利福尼亞州莫德斯托城一家汽車游客旅館的房間里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要求播放一盤錄音帶,說這盤錄音帶將會證明,瓊斯敦的那些人并不是受到脅迫而結果自己的生命的。說過這些話后,他也不理會記者的提問就走進隔壁浴室里,用一顆子彈打穿自己的腦袋。三小時以后他就死了。 普羅克斯(31歲)就這樣成為瓊斯敦悲劇最近的一名死者。 普羅克斯死后第二天,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周刊》和《紐約時報》就得到了他要求發表的那盤錄音帶的復制品。這盤43分鐘的錄音帶錄下了瓊斯敦最后極度痛苦的掙扎;并且清楚地表明,瓊斯要求他的門徒們喝下摻有氰化物的果子汁進行“革命的自殺”。 普羅克斯以前是電視記者。1972年,他去做披露人民圣殿教派內幕的工作,不想卻留下來成為一名虔誠的信徒,并且很快升到主要新聞發言人的地位。當瓊斯把門徒們集合起來進那致命的圣餐時,普羅克斯和另外二人(蒂姆·卡特和邁克·卡特)正奉命攜帶一只手提箱進入叢林。手提箱里裝著50萬美元和一些使他們可以提取人民圣殿教存在瑞士銀行里的700萬美元的信件。普羅克斯后來說,他們把手提箱留在叢林里了,因為太沉提不動。 出事后圭亞那官員曾經逮捕普羅克斯,后來又把他放了。他就于去年12月間潛回美國,近乎隱居般地同他的母親住在莫德斯托。…… 美國公眾紛紛譴責“人民圣殿教”荒謬絕倫的行為,指出這不啻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教主吉姆·瓊斯是不折不扣的殺人魔王!
吉姆·瓊斯原是美國一名基督教牧師。他1931年出生在印第安納波利斯附近一個只有900多居民的小鎮林恩。父親詹姆斯·瓊斯在鐵路上工作,曾是當地三K黨骨干分子。但是父親身體不好,很早去世,留下母親莉娜塔帶著孩子,孤兒寡母地艱苦度日。 母子倆住在一間只有薄薄一層錫制頂棚的小屋里。母親工作時有時無,經常一清早就趕去20英里外的工廠打短工。孩子只好托付鄰居照管。貧窮加沒文化常使農村婦女篤信宗教,甚或迷信。吉姆·瓊斯的母親就堅信靈魂轉世,常給兒子講述自己“前世”的故事。她還說自己做姑娘時,有一次夢見了吉姆的外婆,外婆不顧她連婆家都沒有,就預言她將有一個了不起的兒子,他將糾正世間不平之事。 吉姆·瓊斯與他母親感情深厚,但對父親不以為然。長大后,他稱父親是“卑鄙的種族主義鄉巴佬”;雖深愛母親,卻聲稱她是印第安人。 鄰居馬特爾·肯尼迪是個極其狂熱的基督教徒,并且對《圣經》特別感興趣。吉姆·瓊斯小時候深受這位鄰居的影響,不但按時上教堂而且也被《圣經》故事深深吸引。 吉姆·瓊斯從小向往做牧師,向往發表演說。和小朋友們做游戲時他總喜歡扮牧師,站在那兒向大家吟誦些什么。據說他七八歲就能聚攏十來個小伙伴,向他們發表演說,給他們制定紀律,讓他們按他的意圖行事,有時甚至用木條抽打他們。他還常向他們描述不聽牧師勸告而犯了罪的人將來在地獄中遭受烈火焚燒有多么多么的可怕。 10歲的時候,有一天他把伙伴們帶進一間庫房,打開一個小盒子,盒子里裝著一只死耗子!他點燃蠟燭,為那耗子祈禱,舉行葬禮。 鄰居們回憶說,他喜歡小動物,并且總有許多小動物,走到哪兒都帶著它們。 上中學以后,吉姆·瓊斯對宗教的興趣越來越濃,但他并不是學生領袖。他很聰明,總有些與眾不同的想法,同學們都承認他挺出色。 學校附近有所黑人教堂。14歲那年,一心向往布道的吉姆·瓊斯,在這里找到了第一次實現夢想的機會。一位老黑人回憶說,他嗓音柔和、美妙,他似乎總是面帶微笑地對人說:“叫我吉姆好了。” 1949年,吉姆·瓊斯進入印第安納大學。據說他用了十年時間,斷斷續續地聽課,才最終獲得學士學位。他去一所醫院打工,遇到護士馬瑟琳·鮑德溫。她也是一位狂熱的教徒。他們很快相愛,并且結婚。 吉姆·瓊斯婚后不久開始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市衛理公會教堂供職。他熱心幫助窮人,并反對種族歧視,結果卻招致教會內部一些頑固保守派的排斥。于是,瓊斯決心要建立自己的教堂,一所真正自由、平等的教堂,一所黑人也可以進入的教堂。為此,他挨門挨戶的募捐,并兜售小動物。一只小猴子賣29美元。而頑固保守派們則大倒其亂,甚至弄翻他的自行車,扎破他的車輪胎。 1953年,22歲的瓊斯終于在北新澤西街建起了一座小教堂,取名“國民公共教堂”,自任牧師。據說去這所教堂的盡是些貧窮無助的可憐人,譬如一些“又肥又丑的,在世界上沒有任何親人的老太婆。他大老遠走過去又抱又吻,就像是他真的愛她們似的”。 他的教堂隨時為饑餓的人提供食物,幫助失業的人尋找工作。對于有病的人,瓊斯所能提供的就是信仰療法。教堂中的活動不分種族,黑人白人同席共座。 瓊斯和馬瑟琳自己有一個孩子,又陸續收養了8個不同種族的孩子,其中不單有黑人,甚至還有朝鮮人。后來,他的朝鮮族孩子在車禍中死了,他竟找不到一位白人殯儀員來為她下葬。這使他更加仇恨種族主義偏見。 他的反種族主義行為給他的教堂招徠厄運。他受到當地種族主義勢力和教會頑固保守派們的敵視,迫使他的教堂幾次搬家。但是,他同時也開始擁有許多忠實的追隨者。1960年,當他的教堂搬到北特拉華時,他第一次使用了“人民圣殿”這兩個詞,教堂全稱“人民圣殿純福音教堂”。吉姆·瓊斯站在講壇上一板一眼地宣布:“愛就是福音書的真諦,是唯一的真諦。” 20世紀50、60年代美國社會反動、社會問題嚴重。這只要稍稍回顧一下就足以了:首先是麥卡錫主義和朝鮮戰爭,隨后是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因種族隔離而引起的1957年小石城事件和由小石城事件而掀起高潮的黑人民權運動,接下來還有越南戰爭。這正為吉姆·瓊斯的崛起提供了機會,也給他的早期活動賦予了不少進步色彩。不怪有那么多人輕易投到他的麾下,并進而被他的“超人力量”“感化”得心醉神迷。
事實上,年輕時代的吉姆·瓊斯是一個思想非常復雜的人物,他一方面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接觸過馬列主義,并閱讀《資本論》;一方面又希望凌駕于眾人之上像位救世主,于是研讀希特勒《我的奮斗》,學習如何操縱群眾。他一方面對正統神學理論頗有興趣,更是一位《圣經》愛好者;一方面又竭力尋求行“神跡”和“信仰治病”的妙方。 1961年,吉姆·瓊斯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已經挺有影響,還一度成為“城市人權委員會”主席。年底,他又帶著妻子、兒女一起去了巴西,在里約熱內盧講授福音課。他一家人生活儉樸,卻樂善好施。他常常站在街上與當地孩子們對話,也常常走街串巷地探訪居民,了解他們的困難,并設法幫助他們。當地人都感動地說他是“基督的使者”。直到1963年他才回到美國。而在歸國途中,他順訪了圭亞那。那兒的非常原始的熱帶叢林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從巴西回來,瓊斯對美國的現實更加不滿,說這是一個邪惡的國度。同時,他自己也不再僅僅是個基督教徒了,他自己就是基督。他向人們暗示,他就是“可能的上帝”。 吉姆·瓊斯先在一次小規模的骨干會議上對他的助手們說,他清楚自己以前都曾轉世成哪些人,并警告說:“當然,這是非常可靠的,不能告訴別人。成員們不可能理解,特別是最后一次化成肉身。” 在下一個星期做禮拜的時候,他宣布將向出席的人們告知他最大的秘密。經過了一些繁瑣的儀式后,他十分鄭重地宣布道:“我早已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來到世界是為了一種特殊的用處,追隨我的你們是我的選民。你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我化身之前就跟隨我了。我在幾千年前化身為佛,后來我短期化身為巴布,即為建立巴哈信仰的人。我曾經在世上生為耶穌基督,我最后一次化身為俄國的弗拉基米爾·列寧。”他說這些話的神態非常權威而誠實,人們都信了他。 瓊斯說:“我有對社會問題的回答。有一天我將是美國的統治者。我將消滅種族主義、政治壓迫、生態不平衡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我將使全國變得像我們的社團一樣,我把這叫做‘使徒的社會主義’。” 與此同時,他想方設法制造各種“神跡”,尤其是治病。據說甚至連雞心都拿來冒充腫瘤。他的“神跡”被信徒們廣為傳言,而傳言又是越傳越神。 1965年,他預言明年將發生社會大崩潰并爆發核大戰,世界將在大戰中滅亡。隨后他就帶領30名骨干到加利福尼亞州的紅杉谷,建起一座“人民圣殿基督教堂”和一處教團營地。他說,這是唯一可以躲開災難的地方。 曾經也是人民圣殿教骨干分子、后來認清該教面目而主動脫離教團的珍妮·米爾(迪安娜·默托)在一本書中描述: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哪個教堂里黑人和白人隨隨便便地慘合在一起。我從來沒有見過哪個牧師是坐在講壇后面。唱詩不唱傳統的贊美詩,唱的是當時的流行歌曲。伴奏不用風琴,我們聽的是一個樂隊的演奏,這個樂隊一定在舞會上伴奏過。孩子們不是坐立不安地呆在父母身邊,這里的孩子都安安靜靜、彬彬有禮地坐在一起。 瓊斯開始宣講—— 詹姆斯王的圣經充滿了矛盾與錯誤……如果有一位上帝在天上,你認為他會讓我說有關他的圣語這樣的事嗎?如果有一個上帝在天上,讓他把我擊斃!我由神的啟示而看到,這個國家和世界的其他部分正在消亡。舊金山將被夷為平地。唯一的幸運者將是那些我已在洞見中所顯示的藏在山洞中的人。這些隨著我藏在山洞里的人將從核爆炸后災難性的放射結果中被拯救出來。這個山洞引導我們的教會遷到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小山谷中。我已經指明這個山洞深入地下,我的所有教會成員都將留居在這山洞里直到安全地出來。我們集合在紅杉谷以得到保護,戰爭完了以后我們將是唯一的幸存者。它將使我們的群體重新生活在這個大陸上。 當時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高漲,越南戰爭急劇升級,嬉皮士文化泛濫,頹唐的青年正時興聚居嬉皮士流動營地。于是,許多在現實生活中碰壁的人,對社會現實不滿的人,貧困、絕望的人,感情生活嚴重受挫的人,以及久病難醫的人便都千里迢迢地趕來了紅杉谷。“人民圣殿教”的營地一下子聚集起好幾千人。吉姆·瓊斯也就此名聲大振。 最初來的人都把瓊斯奉為基督,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后來的人也隨著這樣做。吉姆·瓊斯睡眠很少,每天拼命工作,星期天也不休息。他能使人相信,沒有他,他們將被三K黨殺死、被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投入監獄,或者遭逢核爆炸等等。他還鼓勵信徒們把自己的家人也都帶來,組成一個不分階級、不分種族的平等社會。
1971年,吉姆·瓊斯和他的主要助手提姆·斯托恩四處奔走,在舊金山和洛杉磯各建了一處新的十分氣派的教堂。總部也遷到了舊金山。瓊斯租來許多大轎車,讓成百上千的信徒乘上轎車,擺開長長的車隊,在這兩座城市間招搖過市。兩處教堂都很快聚集了數千名新會眾。“人民圣殿教”開始號稱有信徒3萬人。 瓊斯開始感覺到自己的巨大權勢,開始得意于自己的號召力和凝聚力,開始飽享自己一呼百應的領袖感覺。美國政客們一向重視有社會影響力的人。他們傳言:“無論什么時候,你若需要一大群人時,那么就找瓊斯吧。” 民主黨搶先攏住了瓊斯。每當民主黨政治家們需要大批的志愿者、情緒激昂的人群或眾多人的簽名時,吉姆·瓊斯的人民圣殿總不會讓他們失望。于是有人說,在舊金山一提到政治總離不開吉姆·瓊斯的名字。 據說在1974年和1976年的兩次選舉中,有好幾個人都是全靠吉姆·瓊斯才得以當選的。這些人至少包括:舊金山市市長喬治·莫斯科恩、舊金山市警察局長,以及地方檢察官約瑟夫·弗雷塔斯。據說,加州的州長、副州長們也沒少得到他的幫助。作為回報,市長莫斯科恩任命吉姆·瓊斯為舊金山市住房委員會主席。 1975年,“美國宗教生活基金會”使吉姆·瓊斯名列“美國百名優秀牧師”。 1976年,瓊斯又被《洛杉磯先驅調查報》提名為“本年度人道主義者”。 瓊斯的影響力有逾出州界的趨勢。副總統蒙代爾在私人飛機上召見了這位“有為青年”。就連總統卡特也沒有忘記瓊斯,他的夫人羅莎琳·卡特曾十分招眼地與吉姆·瓊斯在一次晚會上同臺共舞,并于1977年4月12日從白宮寫來親筆信: 親愛的吉姆: 謝謝你的來信。在集會期間與你共處的時光非常愉快——希望不久能再與你相會。 你對古巴的評論對我們很有幫助。我希望你的建議在不遠的將來能得到執行。 真誠的 羅莎琳·卡特
就在羅莎琳·卡特親筆給吉姆·瓊斯回信后沒幾天,一位名叫吉澤爾的法國記者為采訪瓊斯和他的人民圣殿教,專程從歐洲飛抵舊金山。吉澤爾的采訪從一個星期天開始: 1977年4月的一個星期日,大約3000名黑人和白人教徒吧舊金山的人民圣殿教堂擠得水泄不通。異常寬闊的講經臺上,一位黃頭發的男青年剛剛為同性戀者作完辯護演說。臺上出現了一位身穿錦緞的女歌手,她接過麥克風,臺下頓時一片寂靜……突然,從我的身后,霍地站起一個戴粉紅色頭巾的老婦,她高聲喊叫道:“這簡直是奇跡!真是上帝的奇跡!這是瓊斯的奇跡!吉姆·瓊斯!你們看,這是個惡性腫瘤,是上星期天在這兒作完彌撒后從我身上生下來的!” 老婦人舉著一塊用手帕包裹著的血淋淋的東西,從驚呆的人群中朝講經臺蹣跚走去……這時,瓊斯出現在講經臺上。他穿一身深色西服,配了件淺色襯衫,滿面笑容的臉上架著一副茶色眼鏡。他那副神態自若的樣子,活像一個黑手黨分子。 我頓時感到心里很不舒服。這里的一切都好像是一出事先排演好了的戲。這場精心安排的鬧劇從上午10點鐘就在舊金山的赫利大街開始了。我來到教堂門口的時候,瓊斯的私人保鏢們已經警覺地站在那里監視擁擠的人群了。進去以后,我發現在大理石結構的教堂里,甚至在接待室,到處都站有瓊斯的保鏢。他們當中有個裝卸工模樣的人敏捷地檢查了我的提包,然后,問了我的姓名、年齡、住址、職業……聽說我是記者,他臉上的笑容頓時凝結了,一直用一種混濁而有幾分恐懼的目光盯著我,監視我沿著鋪滿天鵝絨地毯的走廊進入大廳。 癌癥奇跡的插曲一過,教主瓊斯便開始講話了。他首先揭露了舊金山的納粹黨,這是值得贊賞的。瓊斯講話時,一位穿牛仔褲的姑娘準備給他拍一張照片,但立刻有一個保鏢走上來,用他那雙毛茸茸的大手粗野地加以制止,這種情形使我頗為反感。另外還有一件事,則更使我感到厭惡,瓊斯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結束講話以后,一個禿頂的矮子便開始尖聲喊叫起來:“現在該輪到我們盡義務了……請大家把錢包打開!為圣殿捐款會對你們有好處!”他的話音未落,悶熱的大廳里便響起了“刷刷”的點鈔票聲。人們爭先恐后地捐獻支票或現金。那熱烈的場面真令人不可思議。成千上萬的美元隨著動人的贊美詩的節奏,從四面八方匯集起來。但這些錢將由誰來支配呢? “吉姆·瓊斯是未來理想社會的建設者”,這是第二個星期天教徒們給我的回答。那天,教堂里大約有20人,外面走廊等處大約有100人,或者更多一些。他們的平均年齡在25歲左右,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這些虔誠、和藹但頗為冷漠的教徒,在大理石走廊急匆匆地走著,不一會便都隱沒到隔音門后面,好像是在執行什么神秘的使命似的。 他們拒絕了我采訪瓊斯的請求,說:“他實在太累了,不能接待您。但我們可以給您提供您要了解的一切情況。”看來,也只好先采訪他們了。我被引進了擺著紅沙發的會客室里,有人端來幾杯香噴噴的咖啡。 幾個教徒像一群乖孩子贊揚老師那樣,開始向我虔誠地講述瓊斯的動人事跡:三個月以前,瓊斯患急性闌尾炎,被送進醫院。躺在他旁邊病床上的是個剛剛被送進來的墨西哥人。瓊斯見他痛得連哭帶嚎,便忍著劇痛對醫生說:“先給他做手術吧!”像這類感人事跡還有許多……教徒們還對我說:“瓊斯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每兩天才吃一頓快餐。”正說到這里,門突然開了,一位金發女郎慌忙走進來,說:“他太累了,剛剛暈了過去,請取消所有約會!” 人民圣殿的新聞發言人是一位以前駐海灣地區的電視新聞記者。他眨著一雙灰暗的眼睛對我說:“我離開了那個虛偽的世界,準備同主教大人一道消滅不公正和種族主義。”另一個教徒是個臀部肌肉發達的黑人青年,名叫理查多,今年27歲。“我是洛杉磯人,父母都是酒鬼,我也常在街上打架斗毆。如果不是主教大人,我現在準會蹲監獄的。”桑德拉今年24歲,是個面容憔悴的黃發姑娘。平日嗜好喝酒。她的丈夫因在豪華住宅區行竊被捕,現正在獄中服刑。她說:“是瓊斯的圣殿使我第一次懂得了愛的主義。我們要和瓊斯一起建立一個沒有種族、年齡和膚色障礙的美好的世界。”29歲的蒂姆長著一雙有幾分稚氣的藍眼睛,但他的眼里卻包藏著對越南戰爭的恐懼:“從越南回來后,我一直給自己注射海洛因。后來一位朋友把我帶到這座講堂聽主教大人布道。瓊斯說,‘人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權利’,我非常感動。聽完后,我跑回家,把針頭、針管統統丟進垃圾堆,然后來到瓊斯身邊,像其他人一樣為他效勞。” “那你們靠什么生活呢?”他們嘿嘿笑了起來:“我們什么也不需要。教會給我們提供膳食、衣服,并在城里給我們租房子住(可他們每天要工作14個小時)。……” 大家沉默片刻。杯子里的咖啡已經喝干了。桑德拉嘆了一口氣說:“正如瓊斯主教所說的那樣,一無所有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她說這話時有些遲疑,桑德拉與在座的其他人一樣,氣色不太好。 “請允許我冒昧地提個問題:每個星期天大家捐獻給教會的大筆美元到哪兒去了?”“噢,那些錢嘛,被用來救濟智利的窮人了,被用來為印度營養不良的嬰兒增強體質了,還被用來建立私人診所和學校等設施了。” 但這些回答實在太空泛了。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筆錢到哪里去了……因為他們對主教大人是絕對信任的。 …… 第五個星期天,蒂姆邀請我參觀教會。那天的所見所聞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在擠滿黑人和白人教徒、回蕩著贊美詩和馬丁·路德·金贊歌、以及瓊斯主教親切微笑的教堂背后,卻有著一座城中之城。在這座三層的建筑物里,設有精神病診所、司法機構和社會福利辦公室。此外,還有一所幼兒園,一間水療室以及一個每天向舊金山數千名窮人提供漢堡包的食堂。這里的一切都無懈可擊。但在我即將參觀完畢的時候,卻有一件小事破壞了我極好的印象:我突然發現了一個很不起眼的通道,在它的盡頭有一扇門打開著。我看到那里面是一間巨大而先進的錄音室,其設備的完善和先進程度,完全可以和我在博爾德的電影里見到的最高級的錄音室媲美。我看到錄音室里有十幾個人在忙碌著,于是便朝那個門走去。但里面有個人很快就把門關上了,他的眼光也是那樣的混濁和恐懼。 瓊斯的妻子名叫馬瑟琳,是個護士。她每個星期天都到教堂來。馬瑟琳坐在瓊斯的背后,穿一件領口鑲著花邊的上衣,頗像一個溫澤王宮里和藹親切的保育員。瓊斯向人們介紹:“這是我的妻子馬瑟琳。”這個名字美極了,桑德拉告訴我,他們教會的一條船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什么船?”“諾亞方舟,就是那艘繞南美洲海岸航行,給窮人運送藥品和農業技術資料的船。這條船也給他們送去食品。”“食品?”“噢,是送去我們收獲的糧食。”“從哪兒收獲的?”沒人回答了。在大理石結構的會客室里,桑德拉、蒂姆和邁克彼此相望,誰也回答不出我的問題。 瓊斯認為,“老式的、作為基本單位的家庭,是垂死社會中的過時的殘留物。它使有共同境況的貧苦人民相互隔離,使他們受壓迫,”將來的潮流是窮人們在一種全新的家庭里聯合起來。在這個新式的、擴大的家庭里,人人都是兄弟姐妹,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強有力的關懷備至的“父”。人民圣殿就是這樣一種家庭,瓊斯就是家庭的“父”。然而這“父”已經越來越剛愎自用,反復無常,欺壓教徒是常事,只是教徒們都不愿打破心中的神話和偶像,總把教主的壓迫和折磨當成是對自己的考驗。 瓊斯常常向年輕的女信徒提出性要求,并編造出一套騙人的說法,聲稱那有奇異的力量。他有時會向女教徒提問道:“你想過與教父有關的性問題嗎?”珍妮·米爾說,“我當時才14歲,我知道,他希望有肯定的回答,于是我說:‘是’。” 瓊斯在教內嚴禁同性戀,有發生者要受到嚴厲鞭笞。但瓊斯本人卻完全不受限制。他經常與男伴造愛,還要一些女性在一旁觀看。他解釋說:“我與任何人上床的唯一原因都是為了幫助別人。” 瓊斯不貪財。他從信徒們手中聚斂的大量錢財的確大多花在了各種各樣的慈善事業上。但在他個人名下仍然留下了數千萬美元的存款。
盡管吉姆·瓊斯已如日中天,但他卻越來越頻繁地感到敵人的威脅。他總擔心聯邦調查局或者其他什么特別的政治機構暗中調查和監視他。他甚至在辦公室放了一架望遠鏡,以查看外面街上是否有特務。 他心里的敵人首先是那些不友好的記者。對他們,他主要采取嚇唬的辦法。他讓人將不友好或好惹麻煩的記者的名字都加入一張黑名單,讓人對他們加以種種騷擾和威脅:寫匿名信,威脅將他們拖進某某官司,偶爾還施以人身安全方面的恐嚇。 瓊斯心里的另一類敵人是加入圣殿又離開的人。這些人是“叛徒”,他對他們特別敏感。事實上無論什么理由脫離圣殿的人都會馬上被列入黑名單。他們的私人生活(有時包括垃圾)都有人仔細檢查,以尋找資料來恐嚇他們。為了防止“叛教”,瓊斯采取措施,為教徒們準備了可供“曝光”的資料,包括做愛照片等。 但事情仍要發生。 “人民圣殿教”內部有一個計劃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都是教團骨干,且大多為知識分子。因而,委員會的成員既是瓊斯最倚重的,也是他最要防范的。 默托夫婦倆都是計劃委員會成員。丈夫艾爾默·默托是瓊斯的個人攝影師,太太迪安娜·默托是會計室秘書。他們曾在紅杉谷生活得很愉快,但自從搬到舊金山他們就感覺不對勁兒了。 他們覺得在圣殿里,紀律已取代了“愛”,而瓊斯已越來越變成了暴君。要是哪個人在圣殿開會時抽了一支煙,或是把圣殿的汽車開回來時擋風玻璃上貼了一張違章傳票,或者哪個孩子吃了一個大號漢堡包等等,都要當眾受到體罰。計劃委員會的會議內容越來越離奇。不單是沒完沒了的檢討和批判,以及對瓊斯越來越肉麻的吹捧,而且還開始長時間地討論性生活,委員們被強迫坦白他們對性生活的恐懼和幻想,又要承認說跟瓊斯過一夜不但可以克服恐懼,而且可以保證提高革命熱情。事實上,默托夫婦對瓊斯的性行為以及他對教徒們性生活的干預都非常反感。當吉姆·瓊斯越來越熱衷于政治,而且在政治上越來越表現出好斗的傾向時,默托夫婦對“人民圣殿”就越來越沒有信心了。 1975年春的一個下午,默托夫人打電話給瓊斯的一名助手,聲明她和她的丈夫脫離“人民圣殿教”。這下子不得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勸告”和威脅不期而至。圣殿也連續派來兩個代表團,第一個代表團對他們進行長時間的勸導,第二個則要求搜查他們的住宅,說是教團丟了文件。默托夫婦的生活被攪得一團糟,更被以折磨他們的孩子和揭露他們折磨孩子相威脅。默托夫婦無奈,只好準備了幾份文件四處投訴。 1976年7月4日是美國建國200周年紀念日,瓊斯決定慶祝。他帶領幾百名信徒乘上大轎車,組成一個長長的彩車隊,打出“吉姆·瓊斯牧師的人民圣殿”的大牌子,周游全國。沿途租用教堂舉行儀式,廣招新教徒。車隊到達紐約時得到消息:瓊斯主要助手提姆·斯托恩的妻子格雷斯一聲不響悄悄地離開了圣殿。 格雷斯曾在1972年為瓊斯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約翰。自那以后,她與她的丈夫便日益疏遠,在圣殿也不積極。但瓊斯怎么也沒想到約翰的媽媽會脫離圣殿。他擔心她會把他的私生活和圣殿的財政情況透露給報社,更擔心她會通過法院收回對約翰的撫養權。而關于對孩子的撫養權,格雷斯的確在半年以后聘請律師到舊金山法院提起了訴訟。 吉姆·瓊斯其實非常懦弱,他就像只膽小的動物一樣特別容易受驚。一有風吹草動他就想搬家了。地方是早就準備好的。圭亞那叢林深處這片2.7萬英畝的土地是瓊斯在年初就與當地政府簽訂了長期租約的。格雷斯事出后不久,瓊斯就帶了一批最狂熱的信徒急匆匆地趕去了。 教徒們在林間的空地上搭建了30多所結構簡單的房子。每星期有幾十人到達,半年左右時間就聚集了900多人。一座神秘的小鎮就這么悄然出現在圭亞那的叢林里。人們把它叫做瓊斯敦。瓊斯告訴信徒們,這里將是一個不分種族的、平等的新社會。 在與世隔絕的瓊斯敦,教徒們過著清貧的生活。住宿分成孩子們的房子、單身男人的房子、單身女人的房子、結了婚的人的房子。上下鋪,家具簡單粗糙。每對夫婦之間僅簡單地隔一塊不大的薄布。一日三餐很少有葷菜。 瓊斯要求一年后要自給自足,因而每個人每天都被派出勞作,無非是伐樹、平整土地、耕種和澆灌農作物,或是飼養家禽牲畜等等,就像一般的拓荒者一樣。不同的是,他們還要經常被招到大帳篷里聆聽教主的訓導,并定期開會互相啟發、“幫助”。 在這獨立王國中,瓊斯的權力更加不受約束。他獨占了三間臥室,冰箱、彩電、小轎車樣樣不少。伙食自然也是“特供”的。他更加自由地選擇男女做愛伙伴。而別人要想相互建立性關系,不經他的批準是絕對不行的。更有甚者,他還要求女信徒們開會,交流與他做愛的體會。會上她們不得不說:“我曾與吉姆·瓊斯……,姐妹們,請相信我,這是我所經歷的最棒的體驗。” 人們的各種過錯都要受到嚴厲懲罰,不分男女老少,動輒橫遭毆打。有的孩子只因見到瓊斯時忘了面帶笑容地喊“爸爸”,就被電擊! 教徒們還必須給瓊斯寫一些“感謝信”、“效忠信”、“悔過書”等等。13歲的萊瑞·約翰遜在他的“悔過書”中說:“我非常內疚,因為我經常用零錢買冰淇淋、糖果等。我利用了人們的好意。我還講人們的閑話,……”71歲的路瑟·凱頓寫道:“謝謝你為我們這個美麗的社會主義大家園的所有人提供的這些美好的機會……我們將敬愛你,因為你是我們最好的父親。……我絕不背叛這事業。我只會為這個事業而獻身……” 經過反復“教育”,許多人真的把他們的“父親”和事業看得高于一切。一名婦女偷偷喝酒被丈夫發現,丈夫把她帶到瓊斯面前,讓她挨了100皮帶的責罰。 瓊斯開始在他的訓話中大講外面的敵人,并且成立了一支30人的衛隊。但事實上,這支衛隊的主要職責還是用來加強對教徒們的控制。萬一哪一個人的思想控制不住了,那么還可以借助皮鞭和手槍。
“危險”接踵而至了。就在瓊斯逃走剛剛兩星期的8月1日,一篇揭露“人民圣殿教”的文章在《新西部》雜志上發表,文章引述了很多原圣殿信徒的指控,內容涉及:虐待、身心摧殘、勒索、貪污,以及瓊斯與格雷斯的不正當關系等。文章引述了很多原圣殿信徒的話,有人指出:就連只有4個月大的嬰兒都要挨打,瓊斯總是微笑著注視人們遭受體罰。 格雷斯的丈夫斯托恩沒有離開美國,由于他們夫妻倆聯合指控,法院于8月26日做出判決,命瓊斯把孩子還給他們。 斯托恩夫婦、默托夫婦,以及其他有親屬在瓊斯敦的20多人聯合起來,成立“有關親屬委員會”,并于1978年4月11日發表宣言,譴責瓊斯“窮兇極惡殘酷無情地漠視人權”,使用“肉體和心理方面的威壓手段進行思想訓練運動,以沒收護照和在公社周圍設置崗哨的辦法防止社員離開瓊斯敦,以及剝奪社員的私生活權利,剝奪言論、集會自由。” 瓊斯大呼末日來臨,更進一步加強了對信徒們的監視和控制。鼓勵社員們相互監督、告密,還成立了所謂“革命保衛委員會”,結果又把對“外面敵人”的警惕變成了人們彼此間的警惕。 與此同時,瓊斯反復訓練瓊斯敦的人要視死如歸,不怕自殺。他首先讓大家都寫出“悔過書”和“保證書”,說自己曾經怕死但以后不怕了,寧愿跟隨教主“殉道”。他多次把人們緊急召集在一起,訓話后,要他們喝下某種自制飲料,然后告訴他們那是毒藥。 經過“有關親屬委員會”的不懈努力,終于得到國會部分議員的重視。1978年11月1日,眾議院民主黨議員瑞安通知吉姆·瓊斯,他將訪問瓊斯敦。11月14日,議員從華盛頓出發,同行的有不少記者,包括幾位非常優秀的名記者,還有“有關親屬委員會”的6名代表。17日,議員在圭亞那首都喬治敦會見了瓊斯的律師和代表。經過反復交涉,終于獲準前往。瑞安一行乘坐兩架租來的小型飛機飛往距瓊斯敦還有幾英里遠的凱圖馬港村,再由那兒坐瓊斯敦派來的卡車,前往瓊斯敦。 瓊斯敦為議員等人舉辦了歡迎會,表演文藝節目。議員會見了吉姆·瓊斯,記者們也在場。吉姆·瓊斯臉色難看,很警惕,并說自己將死于癌癥。議員按“有關親屬委員會”開列的名單找到近30人談話。沒有人表示不滿,也沒有人愿意離去。 議員一行被要求回凱圖馬港過夜。然而,就在汽車臨行前,有人偷偷塞了張字條,請求議員帶他們回美國。第二天,記者強行闖入一間老年婦女宿舍,引起爭執。瓊斯在記者們的尖刻逼問下終于垮了:“我覺得遺憾的只有一件事,為什么沒人向我開槍?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公社。我們沒有力量。我們并沒招誰惹誰。可是他們不毀了我們決不罷休……”記者們看到了一個患偏執妄想癥的瓊斯。 這時有人來報告,又有一些人要求離開。瓊斯沮喪道:“讓他們走,讓他們都走。走的越多負擔越輕。都是謊話,一走了統統都說謊話。每個人都有走的自由……”議員安慰瓊斯,“這么大個公社,走20來人,沒什么。” 臨行了,突然有位瓊斯的年輕助手用刀逼住議員。律師等人趕緊把他拉開了。瑞安一行急忙帶上那十幾個敢于要求離開的人,乘車奔往凱圖馬港。 在他們等待和登上飛機的時候,瓊斯敦開來一臺拖拉機,上面有六名槍手。而在要求離開的人當中竟然還有一個是奸細。這些人猛烈開火,議員瑞安和兩位最出色的記者等5人當場死亡,另有12人受傷。 風聲鶴唳的瓊斯敦,在夕陽照射下有些異樣。 高音喇叭中傳來吉姆·瓊斯的聲音,要求所有人到大帳篷緊急集合。衛兵荷槍實彈地站在會場周圍,監視著人們的一舉一動。約兩公斤氰化物被倒進一個裝滿自制果汁的大鐵桶。瓊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大家都必須死。所有的人,一個也不能少。如果你們像我愛你們那樣愛我的話,大家就一起殉道……” 教徒們排起長隊。死神躲在叢林背后輕歌曼舞。 第一個走上前來的是一位年輕的母親,懷里抱著她可愛的孩子。 第一個喝下毒果汁的是那還沒懂事的孩子! 吉姆·瓊斯是最后用手槍結束自己生命的。 沒用他動手,人們一個接一個地按照他的吩咐喝下了那桶有劇毒的果汁。 報紙上說他們集體“自殺”了。美國的法院等權威機構大概也會判定他們的確屬于“自殺”。但是,每一位有良知的群眾,請你好好想一想那真的是“自殺”嗎?假如他們沒有加入邪教…… (原文載:世言編著《陽光下的罪惡:當代外國邪教實錄》) |
|||
|
|
||||
|
主編信箱
本網站所刊載信息,不代表中新社觀點。 刊用本網站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