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鄭茜:從“胡服騎射”到“雅歌儒服”,“遠方之人”如何成為中華文化共同締造者?
中新社北京9月15日電 題:從“胡服騎射”到“雅歌儒服”,“遠方之人”如何成為中華文化共同締造者?
作者 鄭茜 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作出了“吾欲胡服”的重大決定。但王室的非議之聲隨即響起,十分尖銳:“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
這個指責出于“華貴夷賤”的內(nèi)在邏輯,但卻站在“教”與“道”的角度,占據(jù)了思想文化制高點。趙武靈王的回應(yīng)是從現(xiàn)實主義立場出發(fā),認為“胡服騎射”必將“利其民而厚國也”,用民生社稷的利益來為自己作辯解,著眼點是國家前途的戰(zhàn)略大局,顯示出的政治高度同樣不可置疑。
此后,趙武靈王進行聲勢浩大的改革,著短裝、束皮帶、用帶鉤、穿皮靴,一舉建立起中原歷史上第一支以騎兵為主體的軍隊,用趙國軍威大振、國勢大盛來為2300多年前的那場思想文化辯論作了一錘定音的了結(jié)。此后,歷史上再未響起過對于“胡服騎射”的質(zhì)疑,顯示出歷史現(xiàn)實主義的價值共識。而千年之下,“胡服騎射”的故事不斷被后人重述,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在回望自身歷史時一個不能不講起的故事,成為中華文明在梳理自身發(fā)展邏輯時一段不能不書寫的章節(jié)。

那么,“胡服騎射”到底隱含著怎樣的中華文明內(nèi)在邏輯?
站在春秋戰(zhàn)國的歷史背景看,“胡服騎射”逆向開啟了文化的開放性格局,那就是華夏對夷狄的開放,中心對邊緣的接納;它在歷史現(xiàn)實主義的場景下激發(fā)出華夷之間的互鑒、互參、互化,引發(fā)了“華化”與“夷化”的雙重變奏。
站在中華歷史的整體視野看,“胡服騎射”則塑造了中華文化內(nèi)部的包容性政治文化心態(tài),奠定了一個悠久而牢固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那就是兼容并蓄、互鑒融通。

“天下”是一個不拒絕“他者”的開放體系
“胡服騎射”六百年后,中華歷史上演了一場“五胡入華”的大戲。但有意思的是,在十六國爭相擁擠上場的紛亂情景背后,歷史卻演繹出另一條故事線,即五胡紛紛自覺或不自覺地完成了文化轉(zhuǎn)型,實現(xiàn)了定居農(nóng)耕化,幾乎毫無例外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傳統(tǒng),最終大部分融入了華夏。
其中,北魏孝文帝是這一時期“以夏變夷”變革浪潮的激進引領(lǐng)者。他著手制禮作樂,用華夏典章重構(gòu)北魏政治文化,用“黃帝裔胄”重述拓跋鮮卑的歷史記憶。于是,弦歌馬上、短衣騎行的北方游牧者,變成廣袖飄飄、峨冠博帶的儒生士大夫,演出了一曲“雅歌儒服”的史詩大劇。《洛陽伽藍記》記錄了一則有趣的故事:南朝將領(lǐng)陳慶之從江南出使北魏,以為一旦跨過長江,就將見到一個在“夷狄”統(tǒng)治下淪為一片“荒土”的文化沙漠;但走進洛陽,眼前的情景讓他大為震驚,鮮卑人治理下的城市,竟然“禮儀富盛,人物殷阜”。他不由得感嘆:“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這樣,“雅歌儒服”就讓我們看到了一場跟“胡服騎射”方向相反的文化大開放,這是“夷狄”對于華夏的主動投入,是華夏對于“夷狄”的強大引力。而這種引力并非偶然,它源自于華夏文化的一種內(nèi)生特質(zhì),可遠溯西周形成的“天下主義”觀念。在儒家看來,華夏居中、四夷相環(huán)的五方格局,構(gòu)成了一個共同的“天下”;在“天下”之中,華夷之別的界限并非由血緣、世系、族類來劃定,而是決定于是否認同和實踐中華文化。
所以,“天下”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不拒絕“他者”。許倬云先生說過,在中國文化之中,“沒有絕對的‘他者’,只有相對的‘我者’”。正如那些突入長城的鮮卑人,在成為“衣冠士族”后,他們充滿自信地宣稱自己是中華文化的正統(tǒng)繼承者,毫不懷疑地將自己的王朝列入中華序列。所以,“天下”就像是一個無遠弗屆的同心圓,從邊緣進入中心的道路敞開無礙。這樣,“天下主義”觀念就鑄造出了華夏面對四夷的無限開放性和無窮吸引力。正是因此,在中華歷史進程中,周邊民族融入華夏的頻密度難以精確計算。
“胡服騎射”和“雅歌儒服”中的雙向式隱喻
這樣,我們就從“胡服騎服”和“雅歌儒服”之中,看到二者共同構(gòu)成的中華文化雙向式開放格局——自內(nèi)向外的開放與自外向內(nèi)的接納。這就像是一個互化相生的太極,擁有將各個文化端點摩蕩相激、融鑒相生的強大機制,它使文化的內(nèi)部始終郁郁生動,生機勃勃;使文化的外向始終吐納自新,海納百川。
中華文明沒有外向的擴張性和侵略性,為何卻能在內(nèi)聚式、內(nèi)向性的發(fā)展中,始終保持自身血脈暢通,沒有陷入文化運行的阻滯和靜止?這樣一種獨特的文化基因,就藏在“胡服騎射”與“雅歌儒服”的經(jīng)典敘事中。
中華歷史歷經(jīng)數(shù)度南北對峙和分裂,為何卻總能再度聚合,一次次重新走向更高水平的統(tǒng)一與更緊密的結(jié)合?這樣一個神奇的歷史密碼,也藏在“胡服騎射”和“雅歌儒服”中的雙向式隱喻中。
正如魏晉南北朝所展現(xiàn)出的大結(jié)局——在分裂的岔路口徘徊300年后,中華歷史最終愈合了分裂的創(chuàng)口,再造了隋唐更加強大的統(tǒng)一,擴展了文明更加豐富的內(nèi)涵。而那些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則成為中國歷史不可缺少的一環(huán)。它沒有因為不同民族成為統(tǒng)治者而割斷傳統(tǒng),而是讓遠方之人紛紛變成了中華文化的共同締造者和共同所有者。

流貫古今的民族文化交融互鑒光譜色系
中華歷史奠定的往復流注的文化交融機制,促發(fā)了歷史上頻繁浩大的民族交往交流。費孝通先生曾經(jīng)深感用“一地一族”難以解釋中國民族的諸多現(xiàn)象,為突破這一長期的理論困境,他提出了“民族走廊”的學術(shù)概念。觀察這些走廊的人文地理,能夠清晰地看到一個流貫古今的、民族文化交融互鑒的光譜色系。
比如,在過去數(shù)千年時光里,游牧的氐羌從西北出發(fā),一路南遷;躬耕稻作的百越從東南而來,向西移行;種植旱地的三苗從中南、云貴移動,逶迤西來。他們在藏彝走廊上相遇,幾種文化在狹長的西南高山狹谷地帶浩蕩洶涌地碰撞交流。僅就衣飾而言,制皮趕氈原是氐羌發(fā)明的,棉麻織錦本是百越擁有的,挑花刺繡則是三苗精通的。而千百年之后,曾經(jīng)游牧的羌人變成了最好的刺繡專家,羌繡現(xiàn)在成為國家級非遺;曾經(jīng)斑衣彩裙的苗人學會了用披氈抵御高原風寒,大花苗的羊毛披氈上織著祖先遷徙的路線圖。作為百越后代的侗族所佩戴的冠狀銀飾,以及密裥碎折的百褶裙飾,則與苗族高度相似,三苗與百越的后裔到底是誰影響了誰?尤其是,從西北高原遷徙而來的游牧人后裔哈尼族,在與種田的百越相遇后,竟然用1000多年工夫把自己變成最有耐心的農(nóng)民,將整個哀牢山半山腰精雕細琢成“哈尼梯田”,這個舉世無雙的農(nóng)業(yè)奇觀成為令全體中華民族驕傲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

“胡服騎射”與“雅歌儒服”的雙向敘事,交織出中華文明的獨特歷史邏輯:開放共享,交流互鑒,美美與共,亙久堅固。(完)
作者簡介:

鄭茜,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近年來主持“‘中華民族形成發(fā)展史’實物表征體系研究”“民族文物價值體系建構(gòu)研究”等課題,提出“中國博物館人類學”學科建設(shè)構(gòu)想并構(gòu)建研究平臺,引進并主編“博物館人類學經(jīng)典譯叢”;始創(chuàng)“中國民族志電影雙年展”與“中國民族影像志攝影雙年展”系列工程;牽頭策劃組織《何以中華——一百件文物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記憶》《傳統(tǒng)@現(xiàn)代》等精品展覽;出版《中國民族與宗教》《邊緣敘事》等專著。

文娛新聞精選:
- 2025年05月09日 11:26:57
- 2025年05月09日 09:37:52
- 2025年05月08日 15:36:45
- 2025年05月08日 07:48:38
- 2025年05月07日 15:0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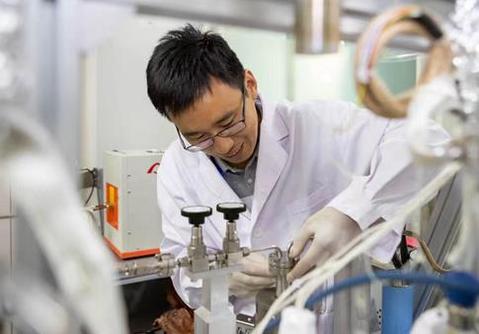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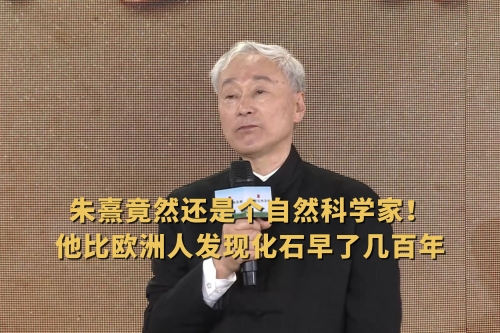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2020092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