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以廈門:從“島詩”到“村詩”
何以廈門?詩以廈門。廈門島嶼的歷史與詩歌同步,因命名行臺所在之島為“新城”,漳州首任刺史陳元光以巡防之所見寫就的《漳州新城秋宴》成為廈門歷史上第一部文學作品。“地險行臺壯,天清景幕新。鴻飛青嶂杳,鷺點碧波真。”島之險要,海之杳渺,鴻與鷺之翩翩,是“島詩”的天然本色。新時期,朦朧詩人在廈門的吟詠留在了文學史,舒婷以“雙桅船”的新意象棲身在港灣的航程與視線里。
對詩歌,廈門人很難辭卻一種情結。“鼓浪嶼詩歌節”傳揚日久,島與詩“再生”在海洋,也“再生”在生活中。
與海相望、相鄰,廈門腹地同安倚村為營,他們“在高山上吟詠”。廈門市同安區蓮花鎮軍營村,海拔900多米,被稱為“離星空最近”的村莊。2022年,“高山紅”鄉村詩歌藝術節來到軍營村。這里有隱約明滅的篝火,有口耳相傳的呼朋引伴。其中有長程的詩歌跋涉者,從1980年代一直走來;更多是被朋友“拐帶”進來的中年“路人”,一不小心,成了詩人。他們是從事兒童詩歌培訓的教師,小學校長,企業經營者,自由職業者……他們是新大眾文藝浪潮里的“大眾”,但他們寫詩不為“爭作弄潮游”。為何而詩?廈門詩人胡翠南以詩作答:“我問為什么寫詩/所有人都笑了,問與答皆不甚了了/但所有人都愿意走向那個空地。”

從軍營村到三秀山村再到頂上村(注:均在廈門市同安區轄內),詩人們用行腳觸探山林、溪澗、田野、菜園,用詩行記取時代在山村留下的呼吸與嘆息。“你的村莊史實在太短暫,缺乏一些老房子考證人世的變遷。你的水源也不充沛,一口大井抱著‘知青’的故事在深深的夜里,睡得很沉!很沉!”(禾青子)“古老村落/正溫柔地被冒犯著/關于空白部分/蟄伏的植物紛紛起身涌入。”(陸十一)這些古老的村落,這片沉默的山野,在新大眾文藝興起的時代撞見這些攜詩歌而來的“村民”。還有多少淮山、茭白、南瓜……等待著“溫柔的冒犯”。
在林立的高樓逆行,在橫渡的海堤穿梭,這座年輕的移民之城,要向山間林地,厚植詩意沃野。“淮山從這片土地長出來/裹滿泥土的溫暖/黝黑的根須也有道場/正悄悄講著詩性的語言。”(黃英燦)“篝火就是這么奇怪/把一群東南西北的人/攪在一起/就升騰成今夜火焰。”(柯友珊)(注:以上均為廈門詩人)誰說只有原鄉才能棲身,凡你醉處,你說過,皆非他鄉。在堅固的生活上空,用詩句網構一座新城。
詩以群分。這座“詩城”分布著性格參差的部落,詩人們各自抒懷,競相欣賞,也彼此吐槽。在詩的國度里,我即是主人。漸漸消散了的,是油香墨跡時代的發表欲望與等待的悠長,渴望的是秒回速評的同情共感。本土的長期駐戶,偶然途經的異鄉人,都被盛情以待,共賞山海。我心安處即故鄉,從島到大陸,跨海的豈止是大橋,是擺渡的詩心,是自創新土與靈根自植。
“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矣。”(《文心雕龍·神思》)廈門,一方是“島詩”,一方是“村詩”,各擅其場,又有多少風云留待村人,或是路人呢。在“新大眾”的才思與神思中,詩人落入凡塵,你我都是路經之人。(完)(《中國新聞》報 作者:陳慶妃,華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文娛新聞精選:
- 2025年04月23日 16:22:22
- 2025年04月23日 16:06:53
- 2025年04月23日 14:22:19
- 2025年04月23日 13:39:48
- 2025年04月23日 11:3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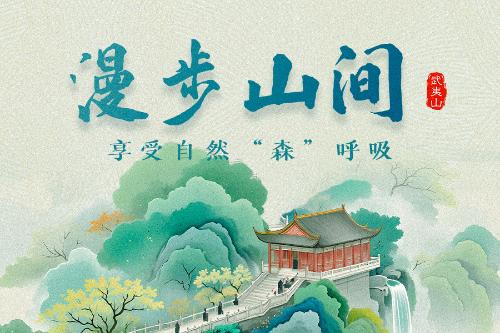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