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先:去北川,書寫“新北川”
2024年底,在北京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多位學者圍繞新大眾文藝展開討論。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劉大先談到數字技術給文學藝術帶來的影響與挑戰。如媒介技術給文學帶來一場“全面革命”,其中蘊含著新的人文取向,即“讓文學回歸到生活之中,與具體的生活發生密切關聯”。
劉大先曾在一個山中羌寨經歷了“數字技術改變文化生活”的具象化時刻。那是2021年至2022年他在四川省綿陽市北川羌族自治縣(簡稱“北川縣”)掛職副縣長期間,一個冬日,他在該縣石椅村偶遇村民殺豬,舉起手機拍照時,一名看起來約70歲的老嫗說,“發個抖音,殺年豬”。劉大先有些驚訝,“這樣犄角旮旯的山里小巷,這個年紀的老太太都知道發短視頻,可見新傳媒能量巨大”。

劉大先將這個小插曲及掛職經歷寫進了《去北川》。這部紀實文學作品去年4月出版,市場反響很好。看到銷量數據,劉大先感受有些復雜:“我以前出版的10余部學術著作,都賣不了這么多。”
劉大先是資深文學評論家,搞長篇“文學創作”是頭一回。他筆下的北川故事打動了許多人。有讀者在網上留言:“讀完這本書,會讓人想去北川,去見見那里的人。”
這正是劉大先想要的效果。“掛職一年,要說能給當地做多大貢獻肯定是談不上。掛職期滿后還能為北川做點什么?我想,那就寫本書,讓沒到過北川的人們了解這個地方。”
北川是我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也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災后唯一異地重建的縣城。掛職期間,劉大先走遍北川下轄19個鄉鎮,記錄下自己經歷地震、洪水和泥石流,以及行駛中的車子自燃等驚險時刻,并解答了他初來乍到時想問的問題:這里地質災害頻發,為何不能以“搬家”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這次寫作,文學與具體的生活發生了密切關聯。作為評論家,劉大先曾提出,進行新時代鄉村書寫,最關鍵的是對人的塑造,讓鄉村的主體自己言說自己。作為創作者,他踐行了這一點。《去北川》中,深入觀察并參與建設的“我”,為了工作“頭發整脫脫,背背整駝駝”的基層干部,質樸、堅韌、追求更好生活的普通人,所有人的言說,為“北川何以成為新北川”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動筆之初,劉大先將這次寫作定位為“有用的寫作”:一方面,從學者角度介紹北川相關歷史地理知識;另一方面,根據掛職期間工作經歷,圍繞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文旅開發、產業發展等,記錄個人視角的觀察與思考,也分享一些實踐經驗。
他發現一些傳統習俗在當地人日常生活中已不多見,而是出現在一些節日慶典、文旅活動中。比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羌年”,這是羌族的傳統新年,每年農歷十月初一舉行慶典。“這原本是一個慶祝豐收、娛神娛己的節日,在羌寨內部小范圍慶祝。如今羌年成了當地的文化名片,慶祝方式依然是祭祀、載歌載舞、分享食物,但外地游客也能參與進來,羌寨居民煮的幾大鍋羊肉,來者有份。”
傳統文化在變化中得到傳承。前述“殺年豬”所在地石椅村,被打造成旅游目的地“石椅羌寨”,傳統民俗展演吸引了大批游客,村中住宿餐飲行業蓬勃發展。
此外,北川根據大禹的傳說和祭祀大禹的古老傳統,打造“大禹故里”品牌和“少年禹”IP等。這些舉措,劉大先參與其中,也寫在了書中。
傳統村落在變化中煥發新的光彩。“傳統就是日常,它隨著人的生活需求發生變化。如果傳統文化不能同普通民眾的生活發生關聯,就不會具有綿長深厚的生命力。老百姓并不在意所謂‘地道’,他們看重的是傳統的東西能不能融合到當下的生活中,給自己帶來便利或利益。所以,我們做保護傳承的工作時,千萬不要進入曲高和寡、陽春白雪的想象中。”劉大先說,“《紅樓夢》誕生的時代,小說還是引車賣漿者看的,不登大雅之堂,如今它被奉為經典,這就是變化。我們不能抱殘守缺地固守在某個階段性文化樣態中,應該敞開胸懷,擁抱新變化。”(完)(《中國新聞》報記者 程小路 報道)

文娛新聞精選:
- 2025年04月21日 17:42:03
- 2025年04月21日 16:47:41
- 2025年04月21日 16:19:32
- 2025年04月21日 11:23:25
- 2025年04月21日 11:0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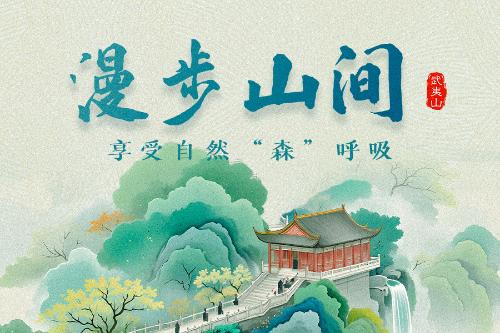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