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創圖作品享有著作權嗎? 法官詳解江蘇首例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權糾紛案
隨著人工智能飛速發展,輸入幾個提示詞、表達清楚構想,就可以借助AI強大的學習、分析和創作能力,迅速自動生成經過個性化改編的文圖新作品。但這種創作模式不免產生新的法律問題——AI生成的作品有版權嗎?
前不久,江蘇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判決一起著作權侵權糾紛案,認定體現創作者智力勞動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具有獨創性,應予保護。該案系江蘇首例、全國第二例認定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具有著作權的案例。
創意被擅自做成實體
“90后”林晨是上海一名AIGC藝術設計者,在AI圈內小有名氣。去年,他偶然發現,之前通過某“文生圖”軟件設計生成的夜晚黃浦江邊愛心氣球的圖片《伴心》,被擅自做成了實體裝置,且被常熟某房地產公司展示于常熟某商業區的水面上,用于相關商業項目網絡廣告宣傳。
林晨立即聯系了制造該氣模裝置的浙江省杭州市某公司,指出其行為涉嫌侵權并要求下架,對方未給予積極回應。咨詢律師后,林晨向公證機構申請了證據保全公證,并于2024年4月向常熟市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杭州某公司和常熟某房地產公司停止侵權,刊登聲明消除影響,判令兩被告賠償經濟損失50萬元等。
庭審中,被告杭州某公司辯稱,行業內早就有相關愛心創意,氣球呈紡錘形,是常見的幾何圖形,由于缺乏原創性和表達性而不應構成作品。其還認為涉案作品本身幾乎沒有知名度,原告主張賠禮道歉遠超合理范圍,賠償金額亦缺乏依據和合理性,且對設計該實體裝置的常熟某廣告公司相關侵權行為并不知情。
被告常熟某房地產公司辯稱,原告創作的圖片不構成作品,其不應享有著作權,認為廣告公司放置的愛心氣膜產品與原告主張的美術作品不構成實質性相似,其主張產品侵犯其著作權不能成立。
判決構成著作權侵權
庭審中,原告詳細說明了其用相關“文生圖”軟件進行設計的過程,由于AI工具的不可復現性,當庭展示了在軟件后臺所編寫的系列關鍵詞,陳述了如何生成夜晚黃浦江邊愛心氣球圖片的過程,并通過不斷修改關鍵詞,對生成的圖片內容中愛心氣球的大小、數量、造型、姿態等進行調整。原告還展示了通過PS軟件對圖片進行編輯的過程。
此外,2023年4月7日,國家版權局對《伴心》概念裝置的圖片進行作品登記,登記類別為美術作品,作者及著作權人均為原告林晨,創作完成與首次發表日期均為2023年2月14日,版權登記圖與《伴心》圖的文字表達一致。
法庭還查明,兩被告被指侵權圖片除了在部分背景設計效果不同外,圖片核心即“水面浮有半個愛心”的部分,與《伴心》圖片內容高度一致。
庭審中,兩被告均承認確有實施案涉愛心氣球裝置的行為,但均稱彼此間未發生直接的合作接觸,而是由第三方廣告公司提供具體設計方案,但均未提交相關廣告合同及廣告公司具體名稱。
法官當庭審查了原告所用的“文生圖”軟件的用戶協議,并登錄創作平臺,對登錄過程、用戶信息以及提示詞修改等圖片迭代過程進行審查,依法認定原告對提示詞(即關鍵詞)的修改,以及通過PS軟件對圖片細節的處理,體現了其獨特的選擇與安排,以此生成的平面圖具有獨創性,屬于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
綜上,法院判決認為,案涉《伴心》圖體現了作者獨特的選擇與安排,具有獨創性,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美術作品,應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兩被告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將該圖片進行網絡傳播構成侵權。原告享有的著作權應限定于該圖片,被告常熟某房地產公司僅以“愛心”為基礎進行實體建造不屬于侵犯原告著作權的行為,結合原告舉證相關合理費用支出的證據,最終判決侵權方連續3天公開向原告賠禮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和維權費用合計1萬元。
判決后,原被告雙方都未提起上訴,目前該案判決已經生效并履行。
綜合判斷作品獨創性
該判決為何認定被告對實體裝置建造不屬于侵犯原告著作權的行為?
該案承辦法官、常熟市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胡越認為,原告享有著作權的作品應當限定為作品登記證書附件所載明的《伴心》平面美術作品,而非半個愛心的立體藝術裝置。
“原告并未就其《伴心》圖進行立體藝術裝置建造并實際落地,即便相關氣球裝置在黃浦江落地,能夠被著作權法評價的仍應為藝術裝置本身,前提是該藝術裝置本身具有獨創性。”胡越認為,本案中《伴心》圖中的半個愛心氣球,僅為簡單的紅色愛心的一半,且有眾多在先案例使用了類似的創意,因此該半顆愛心的設計過于簡單,不具有創造性,不應將半顆愛心的設計單獨評價為作品并就立體裝置建造的行為認定為侵權。
“兩被告在社交平臺、網店等使用的圖片,在可供對比的部分與案涉《伴心》圖高度一致,僅存在大小裁剪、部分素材涂抹、文字添加等細微區別,故兩被告發布的圖片整體構成實質性相似。”胡越分析說,兩被告未經原告許可,擅自通過互聯網向公眾提供權利作品,侵害了原告的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同時《伴心》圖均標注了作者身份,被告在使用案涉圖片過程中,未如實標注作者身份,侵犯了原告的作品署名權。
關于原告主張被告侵犯其作品復制權、發行權,判決書認為,著作權法不保護創意或構思,著作權人不能禁止他人使用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思想或信息。因此,兩被告通過實地搭建等方式將與原告作品類似的創意付諸實踐,既不構成從立體到立體的復制,也不構成從平面到立體的復制,因此對于原告認為實體裝置建造侵犯其作品復制權、發行權的主張不予采納。
“雖然法律不禁止AIGC在具備獨創性時受到著作權法保護,但AIGC的獨創性高低仍應結合具體案情綜合判斷。”胡越分析說,本案中的《伴心》圖雖經過原告不斷更換提示詞或PS修改,但修改的主要部分為水中半個愛心的形狀,愛心本身不具有獨創性,因此最終結合本案具體情況綜合判定了賠償數額。
“本案為審慎認定涉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著作權的典型案例,明確了AI文生圖被認定為作品的前提是應當能夠體現人的獨創性智力投入。”胡越分析說,在“提示詞—算法模型—生成結果—修改應用”的價值鏈條中,AI用戶從操作者升格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者”,有利于激發創作者使用AI工具進行創新創作的積極性,助力人工智能產業在法治軌道上健康發展。
□ 本報記者 丁國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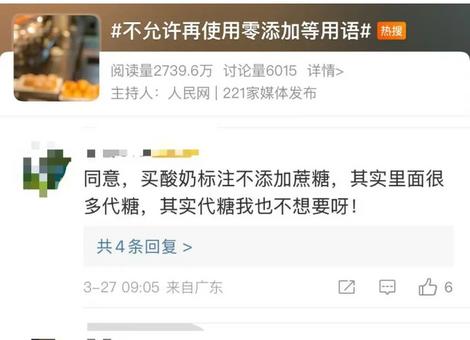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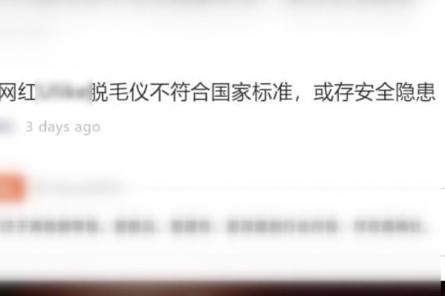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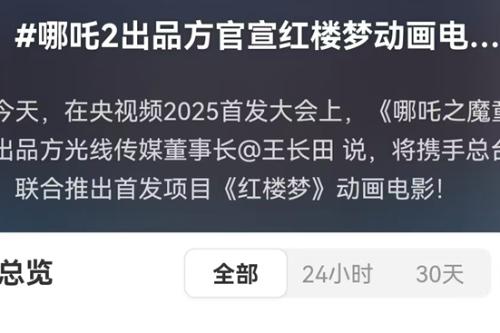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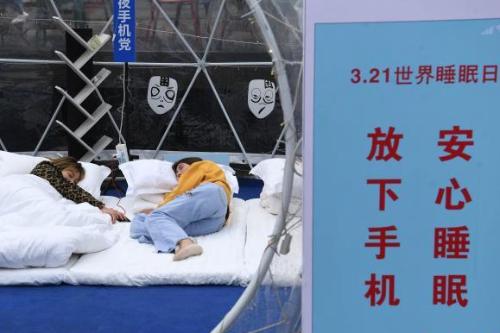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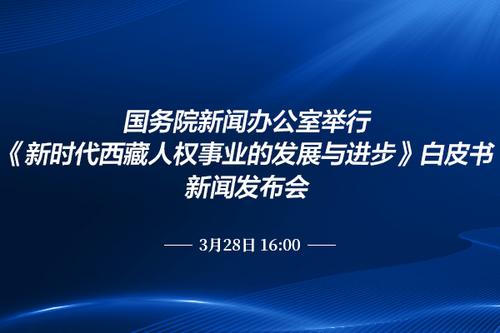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