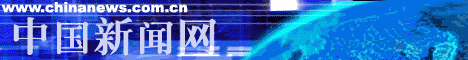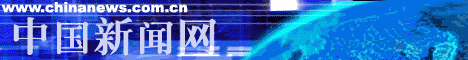中新社北京六月二日電 中新時評:誰推倒了SARS多米諾骨牌?
中新社記者 賴海隆
徐麗(化名)是華北地區SARS幾乎失控過程中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二00三年二月十八日,徐麗從太原啟程到廣州。當時,這位二十七歲的女子并不知道自己正踏上一條充滿SARS病毒與死亡的道路。
徐麗二十三日從廣州返回的時候,SARS已悄無聲息地依附在她的身上。并在此后的半個多月的時間里,奪去了她雙親的生命。同時,她帶回的病毒至少已在四個省市肆虐橫行。到六月一日十時止,這四個省市共有三千四百一十九人被確認為SARS患者,有二百四十四人被SARS奪去了生命。
直到現在,徐麗仍困感不解的是:在她啟程去廣州之前,廣東民間已談SARS色變。可是,除了聽到對所謂SARS傳言的嚴厲駁斥外,進出廣東的徐麗們沒有得到哪怕是一點點的正式警告。
更為可怕的是:當徐麗帶著SARS這種傳播速度極快的兇猛病毒回到太原的時候,整個山西對SARS幾乎沒有設防!后來我們知道,當時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絕大部分省市都對SARS侵入毫無戒備!
徐麗在給中國青年報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始終不能明白,在這個信息從地球南邊轉到北邊只需要二秒鐘的時代,為什么在這些省會一流的醫院,卻沒能得到更多關于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點警告、提示……”。
當發燒三十八度八度的徐麗走進太原一家大醫院,告訴醫生:“我是從廣州回來的,會不會得了‘非典’?”醫生甚至笑了,告訴她“不要大驚小怪。”內心深感不安的徐麗又接連去了兩家醫院,但醫生們都說“不是‘非典’”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SARS作為傳染病,還沒有被北方醫療機構、醫護人員所認識,也沒有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管理,同時也沒有不允許轉院的限制,因此,當徐麗沒有任何防護地從山西轉移到北京的時候,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這樣,徐麗就有了兩個令她自己很不愉快的身份:山西首例SARS患者和北京首例SARS患者。
甚至在北京大醫院的醫生也沒多少人對這種疾病有更多的認識。在將徐麗從三零一醫院轉送三零二醫院時,轉運車輛竟未經任何防護,司機、醫生渾然不知所面臨的威脅。
令SARS幾乎失控的多米諾骨牌終于被推倒了:三零二醫院十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成為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醫護人員。隨后,三零一醫院發現感染病例。四月十四日,天津發現首例非典病人,患者王某此前曾在三零二醫院就醫。
三月十二日,徐麗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出現癥狀,被急救中心送往佑安醫院。隨即,佑安醫院也出現十多例感染患者。三月二十七日,在該院進修的內蒙古臨河市一名醫生返回家鄉,疫情隨之擴散到了內蒙古。
……
痛定思痛的人不禁會問:當時為什么沒有能夠阻止SARS向全國蔓延?盡管SARS是人類尚未認識的一種病毒,但是它已在廣東發作了三個月之久,至少已知它的毒性極強,傳染速度極快,那么,為什么沒有及時向全國通報關于SARS病毒全面真實的信息,乃至發出必要的警告?
不幸的是,在SARS疫情蔓延的初期,直到中央采取果斷措施之前,有關SARS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對稱的,甚至是虛假信息、錯誤信息。
將信息控制住是中國的許多地方官員長期以來在災難發生時的第一反應。發布真實的信息是有成本的,如果在外界得知真相之前就把危機處理掉,這在危機處理中是成本最低的,也能將危機的有害影響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有些官員之所以更愿意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危機,因為它是保持當地GPD產值繼續增長的最好方式,而GDP的產值又反過來維系著一方官員的升遷命運。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官員的思維里出現“GDP大于人的生命”的價值觀也就不足為奇了。
可是,SARS這樣的病毒卻是很難被隱藏住的。你越想隱藏,它卻越加猛烈地爆發出來,以至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嚴重后果是令政府和民眾都沒對SARS病毒對人類的侵入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從而給SARS長驅直入,并迅速蔓延創造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直到中央采取果斷措施之后,那幾乎失控的SARS多米諾骨牌才沒有繼續倒下去。
信息的公開透明是阻斷SARS疫情蔓延的一劑良藥。雖然,民眾在突然出現的一組龐大的疫情統計數字面前,曾經表現出一陣慌亂,但是這樣的慌亂很快就平息了。因為民眾在了解疫情嚴重的同時,也看到了中央地方政府采取的各種嚴厲措施,以及采取這些措施之后所取得的顯著效果。這讓在SARS面前曾經顯得無助的民眾慢慢尋回自信,并開始積極與政府配合,或自發,或有組織形成對SARS的一道堅固的防線。
打破原有的行政條塊分割是有效抗擊SARS的另一個良方。各個疫區不再孤立無援:當北京出現抗炎物質緊缺的時候,立即得到了全國的支援;而一旦北京情況好轉時,又立即將抗炎物資支援全國。更為重要的是,不同地域、不同領域的醫療人員中間,一個互通的信息平臺正在建立,廣東的治療SARS的權威頻繁出現在各地疫區,并將廣東卓有成效的中西醫療法推廣了到全國。
不過,令人深感惋惜的是,這張良方是在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之后才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