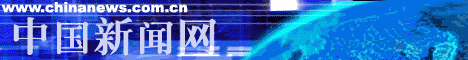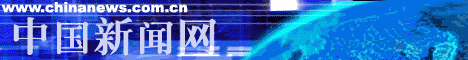做文人,可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因為他的“刀”是筆。做政務官,手中掌握權力,是不能輕易“拔刀”的,因為他的刀可能見血。有權力的人要慎重,要謙卑,要隨時隨地檢驗自己。文人可以快意恩仇,官,卻必須忍辱負重。———龍應臺
沒有社會參與與共識的文化政策是很危險的,因為容易出錯,而文化政策作錯了,是一個城市的內傷。———龍應臺
南方周末:在臺灣的“政府組織”里,臺北市文化局處什么地位?它與大陸各城市的文化局有什么主要差別?上面給的年預算大致是多少?
龍應臺:大約有三方面的不同。臺灣從1999年1月開始實施“地方制度法”,凡是經濟財政、都市計劃、水利交通、教育、文化、觀光等等,都屬于地方自治權限,所以臺北市政府是沒有所謂“上級機構”的。文化局因此也相當獨立。此其一。
臺北市政府本身有三十來個“一級局處”,文化局是其中之一。局處首長是市長任命的“政務官”,當民選市長卸任或去職時,必須隨同離職。局長獨立擬定、執行政策,而不是被動地由市長指揮。政策推動不力時,以去職表示負責。所以相對于市長,局長也是相當獨立的。此其二。
臺北市文化局負責擬定全臺北市的文化政策,范圍包括國際文化交流、文化產業發展、古跡及文物保存、都市風貌的維護、公共藝術的審定、藝術教育的推廣、表演藝術團體的扶植、城市文化設施的興建及管理。相對于大陸的文化局,范圍廣得多,是“大文化局”的概念。此其三。
預算不是“上面”給的。局長依據自己的政策,估出執行政策所需的費用,編成預算,再去向市府和“議會”進行說服和爭取;爭取到的,就是這個城市的文化預算。在過去的3年中,文化局每年有13億到15億臺幣的預算要執行。
南方周末:在文化領域,什么是官方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在歐洲,政府對文化介入似乎多一些,比方在扶助博物館等方面。相對的,在美國,政府的介入很少,介入多是基金會一類民間機構。那么,官方是聽任文化藝術“自由”生長,或者還是要“管一管”,這里是否有一個界限?或者藝術從來不是天然生長的,永遠是需要“人為”的扶助,和“人為”的規劃?為什么呢?
龍應臺:我相信一個重要的原則:凡是民間能做的,政府就不要做。只有在民間沒有能力做,或者因為無利可圖而沒有意愿做的,政府才應該介入。除此之外的介入,都可能反而斫傷了民間的生機。
文化需不需要“管”?要小心。如果“管”的意思是由政府來提供文化發展的條件,創造藝術創作的環境,那么,是的,文化是要有人“管”的。
譬如說,英國政府規定彩券收入的28%必須用在文化上,許多博物館就得以生存,年輕的藝術家也得到創作的補助。譬如說,瑞典立法嚴格保障智能財產權,作曲家因而能夠專心創作;規定圖書館中每一本書的借出,書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報酬,作家因而能夠有尊嚴地生活。譬如說,德國政府高度補貼劇院的開支,使得低收入的國民也買得起票、看得起戲,國民的藝術教養因此得以提升。
我們在臺北市推出了“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后,房地產的開發商就不再敢把百年老樹任意砍伐。把成立文化基金會的門檻從兩千萬元降低到500萬元之后,文化性質的民間基金會就如雨后春筍一樣發展。制定了公共藝術的法規之后kk譬如說,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須用在公共藝術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藝術的品位,公共空間不再隨意地被難看的東西填滿。設置新人創作獎金,藝術和文學的創作者就得到鼓勵。改變稅法容許企業對文化的捐贈抵稅,企業對文化的捐贈馬上倍增,美術館、博物館就多了起來。
再譬如說,政府預算是有限的。修公路、建機場、造學校、蓋醫院,都需要錢。文化不是硬件工程,一般執政者看不見它的重要性,就不會有文化預算。專職的文化機構必須強力為文化爭取預算,這也是“管”的一部分。
這些法規和制度的設立都是政府的積極作為,而且也只有政府能做。這種“管”,是扶植,是培養,是促成,做得好,可以使文化突飛猛進。
文化專職機構最重要的任務是:透過制度和法規的建立,創造出一種環境讓民間力量得到最蓬勃的發展。政府提供最肥沃的土壤,讓民間創意著床、發芽、開花。關鍵在“民間”二字。政府所有的措施,不能忘記它的目的:讓民間壯大。如果文化專職機構積極作為的結果是造就“大有為”的政府而使民間力量萎縮,那么我們寧可不要文化專職機構。
政府永遠不該忘記自己是土,只是土,民間才是花。土是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至于你說美國和歐洲不同,應該是英美和歐陸的不同。歐陸國家將文化看做教育,認為國家應該負責;英美比較把文化看做個人修養。另外,英美的企業捐贈風氣非常蓬勃,私人企業的各種基金都支持文化藝術,政府也就可以退居第二線,預算也編得少。歐陸的捐贈風氣沒有英美盛,國家的投入相對就大。法蘭克福市的年度文化預算,譬如說,就占市政整體預算的10%,非常驚人。
南方周末: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在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的前提下,給了文化專責機構一個行使“文化平權”的機會,也恰巧使您能夠利用官權力把一些原本屬于中產階級消費的藝文項目有意識地下放到民間底層社會?比如,您曾經讓交響樂團到臺北士林夜市的廟前廣場演奏五重奏等“高雅音樂”,讓貧困者也有機會得到藝術啟蒙。我們不否認這個絕好的動機,但基于有不同的欣賞水準,此舉得到的效果是否形式大于內容?
龍應臺:讓我們出身自維也納和茱利亞音樂學院的交響樂團員到“下里巴人”所在的市場里去演奏,有這么一個理念在后頭:如果你是民間私人樂團,臺灣有好幾個民間自組的交響團,你可以高興為誰演奏就為誰演奏。身為公立樂團,就不太一樣。納稅人的錢在支持著你,而納稅人并不是只有那些買得起國家音樂廳票的中產階級;菜市場里賣菜的小販也是納稅人。公立樂團有服務市民的義務。他們可以在水晶燈下演出,也應該可以在公園里、大廟前、榕樹下為買不起票的小市民演出。藝術的教育推廣是公立樂團的義務。
我不認為交響樂、五重奏就是所謂精致或高尚藝術,或者地方戲曲就是低俗的藝術。地方戲曲只要藝術精湛,一樣是精致藝術。把交響樂帶進菜市場,是希望給市民選擇的自由,意思是說,如果菜市場的小販從來就沒聽過交響樂,你又憑什么斷定他們只能聽地方戲呢?有沒有可能,一個在豬肉攤邊長大的孩子,因為接觸到了交響樂,將來成為音樂家,就譬如魯迅在紹興鄉下看野臺戲,得到了他的美學啟蒙?
我是因為市場里聽得到流行歌與地方戲曲而聽不到西方古典音樂,所以才把交響樂帶進去。我同時也把歌仔戲kk臺灣最“鄉土”的地方戲,從廟埕里請出,讓它在知識階層聚集的、最現代的市中心廣場上演出,讓中產階級認識,而且學會欣賞,所謂“下里巴人”的藝術。重點不是把所謂“精致藝術”帶進市場,重點是給人民選擇的可能。
我們打出一個口號,“文化就在巷子里”,一年52個周末,各種形式的表演———傳統的、現代的都有,還有展覽、詩歌朗誦、文史哲的演講,到全臺北市的各個生活角落里去發生。圖書館、地鐵廣場、公園、廟埕,古跡,無處不可演出,無處不是文化。因為是長期的深入,所以就不會有你說的“徒有形式”的問題。“文化就在巷子里”現在還持續進行著。
南方周末:如果文化或者文化教育不能像西方社會那樣在社區基層扎根,底層市民行使文化的選擇權從“你給”過渡到“我要”這個過程是不是有些底氣不足?我們知道,在您的任期內曾經把推動藝術在基層社區扎根作為一項重要施政目標,但效果不理想,我們想知道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您原本有什么構想?我們知道,在臺北文化施政期間,您經常把上海、香港、東京等城市引為參照系,在上海幾乎每一個社區,都有小型的文化體育設施,在每個街道都有圖書室、文體活動室等等,我們想知道,這些社區文體設施是否在臺北一樣發達?在文化平權的前提下,如果今天您是上海市的文化局長,是否也會主張將所謂的“高雅文化”直接帶到最基層的社區?
龍應臺:“全民美育”是我的目標。蔡元培先生早年也提出過以美育替代宗教。當人民的平均文化素養高的時候,他舉手投足之間都是禮,生活環境中舉目所及之處都是美,但這要好幾代的累積。我說對過去3年的社區扎根不滿意,指的是,我們“文化就在巷子里”做了很多,但是還沒來得及將社區中本來就存在的大大小小民間組織,譬如讀書會、家長會、消費者聯盟、文史工作室等等,串連起來發揮力量。
上海的文化設施與臺北作比較?不太好比,因為兩個城市的基本結構就不同。臺北的民間社會,相對于上海,是很大的。因此絕大部分的市民所需,不是由政府提供,而是由民間自營。舉一個例子,臺北的出版社和書店特別多,人們習慣買書,對圖書館的需求就會相對減少。游泳池、健身房等等也都是民間自行運轉的服務業。
如果我是上海的文化局長?上海的文化局長并不掌控上海市的整體文化政策,所以您大概是問,如果我是上海負責文教的市委副書記吧?這個假設有創意,好玩。
這樣說吧,不管我負責的是上海或是北京或是吉隆坡,是的,“文化權”的平等都會是一個核心理念。我們現在經常談的是“人權”,少有人談文化權,但是文化權的平等事實上寫在1948年的《聯合國憲章》中。
文化官是一個資源的再分配者,就是說,人民把血汗錢以繳稅的形式交到你手上,你要決定如何分配這個資源。你必須有兩個面向的思考:一是,怎么用,才能保障這個城市的永續發展;譬如說,現在要做什么樣的投資才能使這個城市在20年、30年后仍舊保有文化上的優勢?人才的培育、創作的獎勵、文化產業的調查研究等等,都是要作長程規劃的。
第二個面向就是,納稅人的權利有沒有被照顧到?如果說,中產階級有劇院、音樂廳、游泳池可去,那么15歲以下的人得到什么?65歲以上的人可以去哪里?坐輪椅的殘障者、拄著拐杖的盲人,得到什么?居住本城的外國人得到什么?外籍勞工、本籍苦力又得到什么?失業的工人得到什么?
文化權是平等的,每一個納稅者都可以要求。連因案坐監的犯人都應該有文化權。一個當權者如果只看到資產階級,他就會拼命蓋富麗堂皇的大劇院、音樂廳等等,而社會里其他的族群kk弱勢的、邊緣的、另類的kk就遭到漠視。如果在這個城市中,資產階級其實是少數,那更有問題了,你就是在用多數人辛苦掙來的錢在服務特定少數的人。
為了將資源作合理的分配,我們需要科學數據。城市里究竟有多少傳統戲曲的欣賞人口?如果經過調查發現事實上有500萬昆曲欣賞者,而城市中沒有一個像樣的昆曲表演廳;如果調查顯示西洋古典音樂的欣賞人口只有100萬,而政府花了巨大的預算興建了古典音樂廳;如果調查顯示出城市里有300萬身心障礙者,包括精神病患,而沒有一個表演廳設有足夠的殘障廁所,沒有一個表演節目用手語;如果調查顯示城里有400萬低收入的外來人口,而這些人沒有任何文化場所可去,沒有任何節目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如果文化預算沒有合理地照顧到全面的納稅人的真實需要,這就是一個有問題的文化政策。
南方周末:我們對臺北當代藝術館實行公辦民營,自負盈虧的經營模式非常有興趣,您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其運營方式?這種方式在文化領域有多大的推廣價值?像博物館珍藏有國有的大量文物,也適用這種經營方式嗎?您力主成立類似文化發展基金會這樣的機構,是否有意讓企業界、民間組織更多地參與文化經營?如果沒有利益趨動,他們會有足夠的積極性嗎?
龍應臺:臺北當代藝術館本來是臺北市政府辦公大樓。市府遷到新樓之后,舊樓經過整修,成為臺灣第一個當代藝術館,也是古跡活化的一個例子。
我當時必須作一個決定:讓這個藝術館和其他美術館一樣,由政府編預算經營,還是釋放給民間經營?政府經營,就是財政的負擔。經濟不景氣,市府歲入逐年在減少。民間經營,一方面民間經營美術館的經驗不足,而且,每年要掏出500萬,又不可能賺錢,誰愿意呢?
我還是希望由民間來經營,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政府的效率不如民間企業,容易官僚化;美術館官僚化,就沒希望了。另一個更重要的考量是,民間力量需要培養。今天他沒有經驗,可是給他一個美術館經營,十年后他就是一個資深的經營者。今天不給他一個機會,十年后他還是不會。譬如學游泳,先給他一個游泳池,讓他跳進去再說。
也是基于這個理念,這3年中我將大約20個政府的建筑釋放給民間去經營,包括實驗劇場、藝術電影院、展覽館、音樂廳等等。民間經驗不足,管理得險象環生。主要是因為,懂文化的人不懂經營管理,而懂經營管理的人又不懂文化。但這些都在我的估算之中。我把這段時期的“險象環生”看做“繳學費”。今天我們的社會極度缺乏既懂文化又善經營的人才,但是有了實習的場域,十年之后就是另一番局面,我們會有一整批優秀的文化管理人才出現。培養民間力量,是要花成本的。
回到當代藝術館。我決定讓政府與民間合作。文化局每年編2400萬的預算,另外的每年2600萬,我找到了幾位有使命感的企業家共同出資,并且組成了“當代藝術基金會”,來經營藝術館,契約先定5年,可以續約。
對這些企業家而言,這里頭完全沒有利益,只有付出。他們以文化來回饋社會。對我而言,因為不是政府經營,所以不受官僚行政作業的限制,彈性較大。譬如說,董事會選出的館長就是一個外國人,一手創設澳洲悉尼當代藝術館的館長。如果是政府,就不能用外國人做館長。
您所說文物的問題,不是問題,因為政府與經營者之間有契約,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都由契約來規范。這個模式是全臺首創,頗為難得,因為一方面要有肯放手的政府,另一方面要有具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才能做成。這決不是說,目前的公辦民營模式沒有問題,有,而且很多,譬如說,如何保障這些館舍不變成謀利的餐館而保持文化用意,就需要政府堅定的把關。
南方周末:您在任局長期間曾一度面臨人少錢少的窘況,但您認為藝文補助也不能雨露均沾,要分輕重緩急;但這個標準如何制定?比如您認為目前臺北在亞洲出版業的龍頭地位已經被上海等城市取代,而臺北的青少年文化活動場所也嚴重不足,而且社區文化也需要補助,在各方要求的情況下,您如何界定藝文補助的次序?
龍應臺:這牽涉到三個層面。首先你需要科學的調查研究。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真正知道你的城市目前的文化結構和體質究竟是什么狀況。過去3年中文化局進行的一件“看不見的工程”就是做基礎調查:文學、視覺藝術、影音藝術、表演藝術等等不同的領域里,有多少創作人口、多少欣賞人口;軟件與硬件,供與求的關系如何。在文化產業方面,出版、電影、流行音樂、廣告設計、畫廊、計算機游戲、觀光旅游等等,產值的曲線為何,趨勢為何。市民的文化消費行為是什么:多少人一個月看幾場戲、買幾本書、聽幾次音樂會;十年后消費行為是否會改變?1800席的劇院對目前的欣賞人口而言是太大還是太小?十年后又應如何?
第二個層面是,你的文化決策者必須有遠見,有國際觀。斯德哥爾摩市的人口只有100萬,卻有八個專業級的兒童劇場,這代表該城對兒童美育極為重視。倫敦花很大筆的預算重點補助25歲以下的創作者,而紐約強力補助青少年買票看戲聽音樂,漢城則選擇補助電子游戲的研究發展。為什么?每一個城市都在設法維持自己的競爭力,看準自己的優勢和弱點,利用優勢,補強弱點。我在任內特別爭取預算作臺北電影節、臺北國際詩歌節,給予民間補助時,專門挑有潛力永續發展、有可能進入國際舞臺的藝術團體等等,是對于臺北市的文化藍圖有一個全面布局的。
第三個層面是,文化政策不能閉門造車,或者由主政者獨斷獨行,它必須有社會共識。不同階級、族群的市民,不同領域的文化界,有不同的困難,不同的需求。過去3年中,我們和最基層的社區市民開過無數次的溝通會議,和文學界、視覺藝術界、表演團體、建筑界、學術界等等的意見代表,對大大小小的議題開過上千次的咨詢協商會議。各種領域的專家學者全面參與文化局的所有決策過程。也就是說,當文化政策以及補助原則推出時,它其實已經融入了各行各界的意見,是一個社會共識的結果。
補助政策只是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沒有社會參與與共識的文化政策是很危險的,因為容易出錯,而文化政策作錯了,是一個城市的內傷。
南方周末:您為什么認為“臺北是文化沙漠的玫瑰,跟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比較起來,是華文版圖上對于中國傳統中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城市”?那么,大陸的曲阜和西安算不算中國傳統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城市,雖然這些城市的文物古跡在城市化浪潮中也曾遭到一些不同程度的破壞?
龍應臺:到過臺北的大陸文化人kk如果他不是很倒霉地每天都在跟人吃飯的話———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觀察:臺北是傳統中國文化保存得最厚的地方。我記得莫言說過、王安憶說過,還有許多來開會的學者。他們指的當然不是古城古跡kk臺北怎么能跟西安相提并論?他們指的是看不見的文化內涵。臺灣保留了許多傳統:宗教,不論是佛教或道教,一樣的昌盛;教育還教孔孟儒學與古典文學,孩童還上孔廟朗誦三字經與唐詩;尊師重道、出悌入孝仍是主流價值;待人接物、語匯用詞仍是舊時規范。
可以說,臺北是一個非常“中國文化”的城市。
南方周末:在《當權力在手》一文中,您對政務官、事務官、民意代表、媒體、作家這幾個不同角色的定位及權責作了精辟的分析,這是來自3年多的政務官生涯帶來的收獲嗎?因為在初掌文化局權力的初期,我們經常看到的是一個作為政務官的龍應臺與作為一個作家的龍應臺兩個不同角色間的斗爭與掙扎,“議會”抗議事件,石原事件等都有作家龍應臺的影子出現,可后期的龍應臺,越來越像一個政務官的龍應臺,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龍應臺越來越適應官場游戲規則了,那個有著不羈個性與尖銳筆觸的龍應臺也學會政治妥協了。
龍應臺:做文人,可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因為他的“刀”是筆。做政務官,手中掌握權力,是不能輕易“拔刀”的,因為他的刀可能見血。有權力的人要慎重,要謙卑,要隨時隨地檢驗自己。文人可以快意恩仇,官,卻必須忍辱負重。拿文人的放蕩不羈來做官,是不負責任的。要放蕩不羈,就不要做官,因為所謂做官,就是一肩扛起人民的期許,家國的未來,多沉重啊。
我經過角色的掙扎,因為做官太“苦”了,臺灣尤其是個“官不聊生”的地方。但是我很清楚我為何為官——為臺北市的文化遠景打基礎。如果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必須彎腰,我當然彎腰。讀讀蘇東坡的“留侯論”或者“賈誼論”,“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就知道,所為何來。我可不是為了表現個性而去當官的。要表現個性我就該留在作家的位子上。
所幸在今天的臺灣,我必須常常為理想彎腰,脊椎卻總是直的。
南方周末:在這次近4年的官場實踐中,您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最值得您高興及最令您感到遺憾的事情是什么?在臺北市政府的告別會上,馬英九先生笑稱,希望您不要把這幾年的政界生活作為素材,燒起第二把“野火”,但您并未答應,這是否意味著在您正在創作的新書中對此有所反映?離開文壇近4年龍應臺是否還想燃起第二把“野火”?或者手下留情或者有所顧慮,令過去潑辣瀟灑的文風打點折扣?
龍應臺:最大的收獲是我上了完整的一堂政治課。政治里頭有人與權力的互動,有理想與現實的拉扯,有歷史與未來的糾纏,有時勢和英雄的辯證,有可為與不可為,有法家和儒家。我上了一課,這一課,再多的書本也教不來。
最大的遺憾?沒有。
或許有,還沒回過神來,人又老了三歲。
第二把“野火”?文章風格改變?等著看文章吧。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朱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