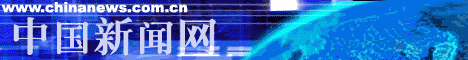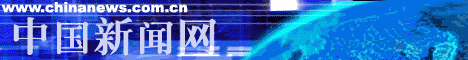美麗的西子湖畔,一間茶香四溢的小茶樓里,我再次見到了導演張元,讓人吃驚的是,他那一頭標志性的爆炸卷發竟被刮去,成了一個光頭。去年張元一改地下邊緣的路子,一連氣拍了三部風格迥異的片子,其中有關于愛情的《我愛你》,有即將公映的懸念型的《綠茶》,最夸張的是京劇《江姐》。當然這還不算,現在他又突然轉行改拍電視劇了!這部在杭州拍攝的《閃》被歸為全新人的偶像青春劇,還組織了一個國內挑戰F4的閃5組合。連張元這樣的導演都開始超乎常規,玩弄起商業的東西了,這就更讓人想一探張元的新路數。于是我們的話題便先從他那留了幾十年的爆炸頭被剃凈開始了。
剃光頭為了支援抗非典
記:不明白您的那個留了30年的爆炸式怎么給剪了?一般人剪發好像都是受了一定的刺激。
張:我用剪發來堅決抗擊非典!
記:哦?這之間能有什么聯系?不明白。
張:非典的時候鬧得我的《綠茶》沒法如期放映,我就剪發明志抗擊非典。非典期間我又刮了一次,抗非典斗爭就勝利了。
拍電視劇是盛情難卻
記:您之前拍了那么多曲高和寡的文藝片,您是怎么想起來拍一部那么商業的電視劇的?
張:其實我覺得拍戲不應該有太多限制,你們做記者的可以寫小說,那我們做導演的同樣是拍故事,無論是拍紀錄片、短片、音樂片,還是電視劇都是表現的方式,藝術本來就是自由的,所以無論哪種方式都可以。如果別人還沒給你限定呢,你自己就把自己限定了,那你的結果就只有死亡一種。
記:可是電影和電視劇的確從欣賞人群的層次上是不同的。
張:不要把電影看成是很高的東西,它也同樣是要靠別人來欣賞的,如果電影拍出來都沒人看,那還有什么意思。
記:您是不是就有這種感受。
張:對,我不希望我的電影拍出來沒人看。
記:那究竟是什么吸引您來拍這部電視劇的?
張:我從來沒有因為一個理由去干一件事,每次都是有很多原因的。
記:那原因有哪些呢?
張:最早是朋友來找我,盛情難卻。后來是覺得劇本有意思,然后自己也有了想法。我這人不經勸,最后周圍的人也都說還行,我就去了。
平民化才能打動人
記:從您之前的《東宮西宮》、《北京雜種》等許多邊緣題材的電影,到起用大腕、明星的《綠茶》、《我愛你》,再到現在您拍的這部電視劇,您是不是覺得自己也對中國電影的現狀做了一些妥協。
張:我1989年從電影學院畢業,經歷了很多,我是逐步發現,真的能夠打動你情感的往往是那些平民化的東西。如果一個文化人不去接觸打動你的最基層的感動,你就很難有理由站在任何高度去評論任何文化的東西。我也一再跟大家說,不要把電影看成是很高很高的東西,它可能是個將要死亡的東西,特別是以藝術化自居的那些成天拍攝大眾根本看不懂的電影的人。
記:為什么這么說?
張:其實這話不是我說的,是前年我在莫斯科電影節做評委時,聽到大師安東尼奧尼的一句話:電影說不定可能是快死亡的藝術,尤其是那些以沉悶為代價的所謂的藝術電影。當時我聽到這話時就比較震驚,但現在我很同意這句話,以沉悶為代價,本質就是以拒絕大眾為代價。
《閃》劇并非青春偶像劇
記:作為一部青春偶像劇,為什么會用《閃》這個名字,許多人都想知道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撤?還是閃亮?
張:(笑)這部戲原來叫《黑眼睛》,但我覺得“閃”更能表現故事中人物情感的閃現。這部戲首次涉及了法律援助,應該說故事本身并不輕松,是關于社會的大主題。說到青春偶像劇,這是制片公司的一種宣傳噱頭,我并不完全認同這種定位。
記:但您在《閃》中起用了5位新人,并力圖打造成挑戰F4的新偶像組合“閃5”,是怎么想起弄這么個偶像組合的?
張:我覺得對于電視劇,新演員非常重要,他們的新鮮感是讓觀眾鎖定頻道的法寶之一。觀眾看明星表演,往往是看明星而不是劇中的人,新人容易與角色融合在一起,能帶動觀眾入戲。我用新人的自信在于投資方認可我,我也曾讓一批新人從我的電影里脫穎而出,我有經驗。
記:那目前這些人是不是已經有了包裝的公司及推廣?
張:也沒有吧(皺眉),當時我挑選他們是因為他們的個性和劇中的人物非常像,而且各有特點。我希望他們不是那么膚淺的一個偶像,希望他們演好戲,成為真正的演員。
記:您對這部戲有什么期望。
張:我不太希望從偶像上提高這部戲的名氣,因為這不是我的初衷。我不希望放棄自己當初的想法。當然我希望它有一個好的收視率。
張元檔案
□1963年生于江蘇。自幼學畫。
□1992年拍攝中國首部搖滾影片《北京雜種》。
□1994年被美國《時代周刊》推選為“21世紀世界百名青年領袖”之一。
□1997年,《東宮西宮》入選戛納電影節。
□1998年拍攝《過年回家》。
□1999年,完成紀錄片《瘋狂英語》。
□2000年,聯合國授予張元“文化和平獎”。同年,拍攝數字電影《金星小姐》。
□2001年,完成紀錄片《收養》。
□2002年,完成《我愛你》、《江姐》、《綠茶》,空前地多產、多話亦多爭議。
□2003年初,籌拍其首部電視劇《閃》。劇中的5個新人主演組成一個名叫“閃5”的偶像組合。
來源:北京娛樂信報 作者:宗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