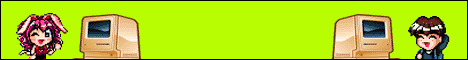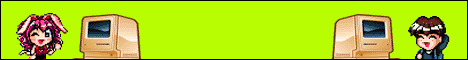(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并注明摘自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周刊》。)
當影視毫不留情地將話劇這門傳統的藝術擠到邊緣,話劇演員演變為影視劇最具實力的大軍時,這位61歲的老人依然堅信話劇的重生,一如等待他的戈多
本刊記者/粲然
話劇《趙氏孤兒》正在北京人藝劇院演出。
10月30日晚7時許,觀眾們都領票進場了,在陸續傳來的舞臺聲響中,劇院越發顯出一種無法抹卻的孤清。
二樓咖啡館里,該劇導演林兆華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他穿著寬松的牛仔褲,套一件大大的毛衣。怎么看,都像個老年“哈韓族”。往來其間寥寥幾個青年,都親熱地叫他“大哥”。
“我以前拍的戲,很多人說難懂。那么這次《趙氏孤兒》會讓所有的人都看懂,而且覺得好看。”
《趙氏孤兒》是最早介紹到歐洲去的中國戲曲,伏爾泰進行了改寫,取名叫《中國孤兒》,并把原先血腥復仇的結局改成了雙方最后諒解。1990年,法國使館的中法比較文學協會成立,委托林兆華執導該劇本,因為喜歡中國戲劇,林兆華最初用河北梆子表現這個經典劇目。北京人藝此次排演的《趙氏孤兒》是他的第二個版本。
新聞周刊:事隔13年,什么原因又讓您重拾《趙氏孤兒》?
林兆華:第一,我看到京戲等幾個戲曲版本,我覺得這個戲老百姓都比較熟悉。第二,一般人認為我的戲不大看得明白,但其實我的戲不是從先鋒的角度出發的。我也想做一個專家們和老百姓都明白的戲。
新聞周刊:您覺得這版《趙氏孤兒》最大的變化在哪里?
林兆華:除了劇情,這個戲功夫下得最大的是表演。以往歷史劇的表演方式,拿腔拿調的語言,形體上的造型,我覺得是比較虛假的。我們多年倡導的所謂主流戲劇,都是那樣表現的。實際上這是對現實主義的曲解。再說得難聽些,就是偽現實主義充斥舞臺。我希望打掉這些東西。
新聞周刊:這次《趙氏孤兒》是否借鑒了戲曲的東西?
林兆華:我對戲曲的借鑒并不是一招一式的借鑒。中國戲曲的一大特點就是空、無。但這種“無”又包容了一切。戲曲舞臺上的一切都是靠表演來表現的,這在美學上是非常可貴的東西。我喜歡戲曲的原因,就是它給我極大自由。它能做到舞臺什么都沒有,而僅僅靠唱、念、做、打表現出來,這對話劇導演是極有好處的。從表演的角度,坦率地說,我不喜歡演員純體驗,我喜歡感覺,演員的創作應該重“感覺”。
新聞周刊:但有人說,這版《趙氏孤兒》是“炒冷飯”,說您開始重復自己了。您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林兆華:他恰恰沒看懂《趙氏孤兒》。
新聞周刊:迄今為止,它的票房如何?
林兆華:票房不算太好。不比原來的《萬家燈火》,場場爆滿。這種歷史題材的話劇,(票房)有時候八九成,有時候六七成。
“像一些古典名劇,如果硬要搬到大劇場,是打不過趙本山的小品的”
1982年,實驗話劇《絕對信號》的成功,無疑是當時一統天下的傳統話劇界的一聲驚雷。當年看過該劇的一位觀眾,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幕話劇在那個年代帶給自己的震動,“那天晚上我是神情恍惚地回到家的。我一直在想,原來話劇還能這么排。”
新聞周刊:您還記得剛畢業到人藝時的情形嗎?
林兆華:我是1961年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分配到人藝的,那是北京人藝的黃金時代。當時我對人藝排的那些好戲簡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每天都有戲演,經典戲劇像《茶館》、《蔡文姬》是排隊買票。最活躍的時候,連大年三十都演戲。現在不成了。
新聞周刊:您什么時候開始單獨執導話劇?
林兆華: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開始單獨執導戲劇。做《絕對信號》的時候壓力很大。開始我們說“這是實驗話劇”,這個“實驗”的意思是說,好了就上,排不好就不上。人藝提供資金,剛開始只在排練廳演,征求意見,反映挺好,才讓公演。
當時小劇場在歐洲挺普遍,我們看投資的錢少,而且小劇場實驗性非常強,給年輕人提供的空間大一點。
新聞周刊:壓力體現在哪幾個方面?
林兆華:那時中國戲劇千篇一律,尤其是在這個很傳統的劇院做。
新聞周刊:做完《絕對信號》您就出名了?
林兆華:不能說出名,這個戲成功了,大家覺得這個導演還成,就給以后做的戲奠定了基礎。《絕對信號》當時影響挺大的,全國各地(的人)都來了。一些專家原來也有兩種看法。一種說,這不是人藝的傳統。還有一些老專家看了,呀,還挺好看的。其實那時候演得也很簡單,就是比過去說出了些新的東西,沒更多的理論。但觀眾反響很好。一百多場,場場爆滿,從1982年演到1983年。
新聞周刊:后來是不是大家一窩蜂都搞先鋒戲劇去了?
林兆華:我想想,孟京輝是90年代開始搞的。但80年代的戲劇文學創作比90年代好,反映現實題材的戲劇比較多。
新聞周刊:您覺得什么原因使90年代后戲劇不好了?
林兆華:很復雜。80年代后有些作者壓抑了那么多年,激情奔放了。而90年代改革開放,電視劇一進入,寫戲劇劇本的人就不多了。
新聞周刊:在《萬家燈火》之前,您排的話劇賺錢嗎?
林兆華:我給劇院做的戲,都賺錢。我自己工作室做的,比如《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等待戈多》、《浮士德》,這些戲都不賺錢。
新聞周刊:您排這些不賺錢的劇本,是因為您覺得這些名劇應該被重溫、被創新嗎?
林兆華:中國到今天為止,還是強調主流戲劇。所以,你既然不排,我就拿到工作室排,自己籌集資金排。我覺得不這樣做是不對的——國家劇院怎么能不演名著?像這樣一些古典名劇,如果硬要搬到大劇場,是打不過趙本山的小品的,所以我在小劇場做,我只做給喜歡的人看。
新聞周刊:有人認為,獨立于國家劇院之外,戲劇工作室的出現更多地是為個人謀取利益。
林兆華:他們賺錢有什么不好?孟京輝的戲吸引很多年輕人,有什么不好?有人批評他。但我說,孟太少了,應該多一點。現在有很多罵他們的話,我不明白罵人的那些人的心理。他們真懂得戲嗎?有些評論家,只要是貼近主旋律的戲,不管多臭,都可以吹捧。而對孟京輝、李六乙那些年輕的導演做的嘗試,怎么就那么刻薄。
當然也有各種原因對戲劇環境的污染,比方過分強調商業化。但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中國的(戲劇)制作人還是初級階段,并沒有把制作戲劇放在文化藝術角度做,從商業角度考慮得更多一些。盡管這樣,獨立工作室的出現也是好的。
“戲劇永遠不會死。我們把戲劇人才圈在戲劇圈內,是非常愚蠢的事”
近十多年來,林兆華的每部戲,都會引來媒體關注的目光。我們無法判斷媒體和觀眾的關注對林兆華個人創作的風格有多大影響。但是,可以看到,林兆華自己多年來的創作軌跡,非常切合于媒體和觀眾趣味的不斷變化。
新聞周刊:這么多年來,哪部戲可以稱得上您的代表作?
林兆華:《哈姆雷特》吧,《等待戈多》、《理查三世》都不錯,還有《風月無邊》那個舞臺。《萬家燈火》不成,那不是傳世的東西,是大眾通俗戲。
新聞周刊:在業內有一種說法,比如孟京輝,他一直樹立實驗的先鋒的旗幟,但看您的戲劇,卻覺得時而非常實驗,時而非常主流。為什么您要這樣做?
林兆華:也不全是,比如《紅白喜事》,實在得要命,舞臺上煙可以冒煙,井可以打出水來。我都是根據戲的需要做的。
新聞周刊:《萬家燈火》熱演時,有人指出,話劇圈有兩類鐵桿觀眾,一類是熱衷傳統劇目的中老年人,一類是部分青年白領。但前者認為您的戲晦澀難懂,后者認為您的戲不夠時尚。兩部分觀眾都背離了您,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林兆華:我就是中庸。中庸之道是非常舒服的。大師的戲我也看過,理論家的書我也看過,但我不按照專家說怎么做,或者一個流派說該怎么做去做。我有自己的認識,我要創造(我的)學術和流派。
新聞周刊:熟悉您的人說您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斷地創新”,您是否因為創新而創新,有搞噱頭之嫌?
林兆華:原來很多教授對我也有一些意見,說我搞形式。我認為這是他們沒形式,所以說我搞形式。可藝術形式是一個藝術品成熟的標志。我們原來只強調戲劇的內容,但怎么可能形式離開內容呢?真正的藝術品都是內容和形式的結合,我們過去就是只強調意識形態,不強調藝術形式。
新聞周刊:您到這么大年紀還在一直創新,是否擔心創造力枯竭的時候?
林兆華:我不擔心。我臉皮比較厚,我做戲沒有負擔。我每當做一個戲,不考慮失敗如何,成功如何。我想做就做了。
新聞周刊:做那么多年話劇,您覺得最無奈的是什么?
林兆華:其實我想說,我覺得無奈的,不是票房,而是體制。中國戲劇體制,早已落伍了。我們有些戲并不比發達國家差,但戲劇狀態還是不行。
新聞周刊:如果體制打開了,觀眾還會回到戲劇中來嗎?
林兆華:戲劇永遠不會死,永遠不會死。我們把戲劇人才圈在戲劇圈內,是非常愚蠢的事。應該讓盡量多的人進來。-
林兆華
了解林兆華,等于了解了上世紀60年代至今的中國話劇史。
1961年,剛從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畢業的林兆華,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工作。那年他19歲。
1982年,政策甫一放開,當年“懷著對經典名著五體投地的心情”進入人藝的他,率先發動了當代話劇史上第一場“造反”:執導了第一場先鋒實驗話劇《絕對信號》,并獲得巨大成功。中國小劇場話劇的演出形式也由此開始。隨后他又導演了《車站》、《野人》等實驗性話劇,同樣反響強烈。
1985年,當“實驗”之風逐漸在中國話劇界盛起之時,林兆華卻排演了現實主義題材的話劇《狗兒爺涅》。而接下來他導演的《哈姆雷特》、《浮士德》及《等待戈多》等話劇,似乎又在向人展示其駕御國外經典的“功夫”。
有人稱他為“中國話劇史上最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導演”,而其不斷在先鋒與現實話劇之間游走的風格,一方面被認為是他駕御不同話劇題材功力的表現,另一方面,也使他陷入既不俗又無雅的尷尬角色之中。
近日由他執導,正在北京人藝上演的《趙氏孤兒》,因為濮存昕、徐帆等名角的加入,也頗受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