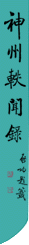小時候寫春聯,我最愛的一副是“又是一年春草綠,依然十里杏花紅”。這副聯語的妙處全在于“又是”、“依然”四個虛字。只是“一年春草綠,十里杏花紅”等實字,就沒有多大意思了,只不過是機械地對仗而已。可一加上虛字,全聯便活了,顯現了一種極為美妙的意境。這正像“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一樣,在原來五字句上,一加“漠漠”、“陰陰”四字,詩境便活起來,在藝術氣氛上就給人以強烈的感染和無窮的想像了。
每到春天,我便常常想到這些聯語,因為春草年年是要綠的。我常常思念著這種意境,也常常懷念著春明的春花。去春思舊詩曾有句云:“記得宣南花事好,丁香應憶白頭人。”日前又得詩數首,中有句云:“異國春情芳草色,頻年歸夢看花心。”不怕人家笑話,人老而風情不老,思念春明花事的心,執著一如既往。
北京春花值得思念的太多了,前兩年每到春來,我都要寫兩篇回憶春明花訊的小文。今春在“又是”、“依然”的感召下,怎能不寫呢?又是芳草,依然杏花。北京沒有梅花;“紅杏枝頭春意鬧”,最占春光的便是山桃花和杏花。而山桃花又沒有杏花的名氣大,因而還是先說杏花吧。
“北京人不相識,錯作杏花看。”這記不清楚是哪位江南人嘲笑北方人認識梅花的詩了,不免有點輕薄口吻。其實只要能帶來春之消息,又何分梅杏呢?北京有十分著名的杏花的地方,那就是大覺寺。寺在西山中旸臺山,其路程是頤和園前北行,繞頤和園北墻到青龍橋,然后到紅山口,直奔西北。其間有黑龍潭、白家僮、溫泉、周家巷,直至北安河村,就到了旸臺山麓了。寺在山凹中,本為金章宗之清水院。寺的周圍,山巒起伏,遠近四方山村,漫山遍野種的全是杏樹。在春暖花開時,一望全是花光。游人騎個小毛驢穿行在杏花中,那境界是蘇州鄧尉山的香雪海所無法比擬的。一是多,最多時花林連綿20多里路;二是高大,老杏樹比梅樹高大花繁,游人著花要仰頭看;三是山勢險要,有的杏花長在懸崖上,下面泉水,清冽如鏡,鄧尉哪有比奇景呢?
昔人大覺寺看杏花詩云:“青山似識看花人,為障風沙勒好春。一色錦屏幕三十里,先生未信是長貧。”“一色錦屏三十里”,可以想見杏花盛開時錦天繡地之景色。過去人們說到杏花,常常盛稱“紅杏尚書”,似乎杏花是紅的,實際在花朵含葩時,是粉紅色;等到盛開時,則是近乎白色的極淡極淡的顏色了。這一點,很像梅花,只是梅花有綠萼梅,而杏花則無綠色的,其花萼都是紅色的。這一點,倒也符合了紅杏之名。
北京春日看花的時間很長,由“紅杏枝頭春意鬧”,到“開到荼薇花事了”,再連上“天棚魚缸石榴樹”的“五月榴花照眼紅”。由暮春到初夏,陸陸續續,為春明花事,可以忙碌兩個來月。杏花、芍藥、石榴等等,這都是普通的大面積的花樹,還不算那些名貴的、特殊的,什么太平花、玉蘭花等等。玉蘭在南方是很普通的,而在北京則比較少見,是認為很珍貴的。京人春游之際,對這些花木,可以按時序花期,次第觀賞。看花雖不能代替穿衣吃飯,但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享受。唱《蘇三起解》,蘇三一挑臺簾唱道:“人道洛陽花似錦,久在監中不知春……低頭出了洪洞縣境。”這沒有自由,不能看花的心情該多么痛苦?
春明三春花事,次第安排,這大覺寺看杏花,不過是一個看花的序幕耳,大軸好戲還在后面呢?
北京春日看花,唯一的一個缺點,就是風多雨少。“杏花春雨江南”,這是江南常見的景致,而在北京則是太珍貴了。杏花春雨,不能說絕對沒有,但是太稀少了,豈不聞“春雨貴如油”乎?那一年碰得巧,正好在杏花開放的時候,落一場春雨,不管大小,都可以挹塵潤土,連空氣都使人感到兩樣,而這是極為難得的。在我在的記憶中,也只遇到過一次。因為杏花花期很短,稍一蹉跎,即便再有雨,也是落英繽紛了。雨不多,而風卻很多,風都由西北方向吹來。冷倒不冷,只是風中都是蒙古草原的黃沙,即北京俗話所說的“大黃風”也。所以“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的境界,在北京看花時,也是難得遇到的。而更多的則是在大黃風中看花,一進山中,因為西北高山屏障,所以風顯得小了。正因為西山不少地方都是背風的,所以花事更繁。正是詩中所說:“為障風沙勒好春”了。杏花——是京華春花的棄,爛漫春色,要次第絢染燕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