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人物丨“詩家”卞之琳:東方意象,西方影響
中新社北京8月6日電 題:“詩家”卞之琳:東方意象,西方影響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天

在二十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的中科院文學(xué)研究所,青年學(xué)子們對(duì)老專家學(xué)者稱“先生”,對(duì)黨政干部稱“同志”,唯有卞之琳例外,大家稱呼他“老卞”。
1929年暑假,19歲的卞之琳考上北大英文系,只身北上,在火車上坐在他對(duì)面的正是剛考進(jìn)清華大學(xué)西語系的錢鐘書。兩人年齡相差不到20天,日后都成為名噪一時(shí)的才子,只是80年代之后,錢鐘書聲名如日中天,卞之琳卻似乎未再回到聚光燈下。
提起卞之琳,可能很少有人會(huì)意識(shí)到,這是一位一直活到2000年、進(jìn)入了新世紀(jì)的人物。他似乎被某種魔法永遠(yuǎn)定格在了“你站在橋上看風(fēng)景,看風(fēng)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mèng)”的《斷章》之中。
他的老友、詩人馮至曾說:“生物學(xué)上有一種孑遺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銀杏、動(dòng)物中的大熊貓,我就是這樣的孑遺生物。”或許因?yàn)楦型硎埽逯蘸苄蕾p這個(gè)說法。他還曾多次提到,年輕時(shí)去看北平昆曲藝人演出,觀者寥寥,幕布上繡著兩句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他每次說起,都有無限的感慨。

“螺旋式上升”
“文革”后,《詩刊》社在北京召開座談會(huì),探討中國新詩的過去和未來。胡喬木作報(bào)告,強(qiáng)調(diào)五四以來新詩的成就,指出新詩壇產(chǎn)生了公認(rèn)的大詩人,分別是冰心、郭沫若、馮至、卞之琳。
卞之琳后來對(duì)友人說,自己稱不上是major poet(大詩人),只能是minor poet(小詩人)。
他的《十年詩草》再版了。他戲仿《文心雕龍》,為詩集起名《雕蟲紀(jì)歷》,稱自己的詩歌“只在歷史博物館或資料庫的一個(gè)小角落暫時(shí)可能占一個(gè)位置而已”。

《現(xiàn)代派詩選》將他的詩列在了篇首,《現(xiàn)代朦朧詩選》則將他的作品歸類為現(xiàn)代朦朧詩。
在這之前,一批境外學(xué)者已經(jīng)開始關(guān)注卞之琳。
香港學(xué)者張曼儀是其中較早的一位。60年代初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xué)東亞圖書館里翻到卞之琳早期著作《魚目集》,后來她和朋友合編《現(xiàn)代中國詩選》,想找尋卞之琳更多的作品,卻著實(shí)不易。《數(shù)行集》是從洛杉磯加州大學(xué)復(fù)制的,《十年詩草》則是從哈佛大學(xué)拿到的膠卷。
荷蘭漢學(xué)者漢樂逸也關(guān)注到了卞之琳。他覺得卞之琳的詩歌有東方意象,又明顯受西方現(xiàn)代詩影響,有明有暗,有陰有陽,耐人尋味。但無論在大陸還是臺(tái)灣,關(guān)于他的詩歌和生平研究都很少,西方對(duì)他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因此,他選擇了卞之琳研究作為博士論文題目。
1979年,漢樂逸前往北京,在一道道手續(xù)之后見到了卞之琳。他告訴卞之琳,想了解他如何用詩體翻譯莎士比亞悲劇。
漢樂逸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卞之琳談了自己的翻譯、格律主張,也回答了不少有關(guān)詩歌創(chuàng)作的問題。
后來卞之琳在一位企業(yè)家資助下,去荷蘭參加了漢樂逸的博士論文答辯。2010年,卞之琳去世10年后,論文修訂稿被引入中國,題為《發(fā)現(xiàn)卞之琳:一位西方學(xué)者的探索之旅》。

“文革”結(jié)束后,卞之琳開始突擊翻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
他1954年譯出了《哈姆雷特》,上影譯制廠的《王子復(fù)仇記》就是根據(jù)這個(gè)譯本整理的配音。有別于朱生豪等人的散文體譯本,他應(yīng)用了自己對(duì)新詩的格律主張,用詩體來譯注。但后來運(yùn)動(dòng)越來越多,他只能擱筆了。到1984年,他總算譯出了《奧賽羅》《里亞王》(即《李爾王》)和《麥克白斯》。
出版的時(shí)候,他頗為清醒地說,自己已有20多年沒有接觸國際莎學(xué),原先知道的一丁點(diǎn)已經(jīng)忘得一干二凈,對(duì)新近的大部分西方文藝?yán)碚撘膊辉敢馄埻虼丝缍?0年的《譯者引言》就算為歷史留痕。
他沒有再譯注莎士比亞其他作品。同為莎學(xué)研究專家的王佐良評(píng)價(jià),在莎士比亞的詩體翻譯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卞之琳。
擱筆20多年后,卞之琳也嘗試提筆寫詩。卞之琳拋開民歌體的束縛,追求用典,尤其講求格律。詩人北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詩歌在押韻、節(jié)奏方面十分嚴(yán)謹(jǐn),幾乎無懈可擊。張曼儀也認(rèn)為,詩歌有西方現(xiàn)代詩的味道,叫人想起奧頓和艾略特的筆法。但二人都指出,或許因?yàn)楦星榻?jīng)過了多年壓抑,這些詩歌無法與他30年代的作品比肩。
1982年,安徽師范大學(xué)四年級(jí)學(xué)生江弱水偶然接觸卞之琳的作品,感受到一種令他耳目一新的高級(jí)感。他正學(xué)寫詩,于是試著將自己的習(xí)作寄給卞之琳求教。三周后,卞之琳給他回信,寄來了《雕蟲紀(jì)歷》,并用鉛筆給他的每一首詩都做了批注。
從此,江弱水與卞之琳保持了十多年通信。現(xiàn)為浙江大學(xué)傳媒與國際文化學(xué)院教授的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認(rèn)為中國新詩100年來,前50年寫得最好的詩人是卞之琳。他覺得卞之琳后期的詩風(fēng)轉(zhuǎn)變是很自然的事情,因?yàn)樗嫘膶⒆约喝谌搿按笪摇敝校瑩肀е袊蟮厣习l(fā)生的變化。
他說,卞之琳深受法國作家安德烈·紀(jì)德影響,紀(jì)德的思想和文字已經(jīng)化為了卞之琳的血肉。
卞之琳曾翻譯過紀(jì)德的多部作品,他非常推崇紀(jì)德,曾在一篇譯者序中如此形容:紀(jì)德的風(fēng)格向來是極富于《圣經(jīng)》體的兩重美處——靈性的熱烈與感官的富麗,像雪白的火焰與金黃的水波。
紀(jì)德50歲之后被認(rèn)為思想兩度“轉(zhuǎn)向”,先轉(zhuǎn)向“左傾”,去訪問蘇聯(lián)后又轉(zhuǎn)了回來。但紀(jì)德自己并不這樣認(rèn)為,他說自己從來沒有改變過方向,而是一直向前走著。
他曾說:“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進(jìn)步。”他在日記中寫道,一種總想調(diào)諧的要求曾經(jīng)折磨著自己。
卞之琳很贊同紀(jì)德的觀點(diǎn)。他說:“順著一條螺旋式的道路走去,在一條曲線上,我們能說到哪一點(diǎn)算是‘轉(zhuǎn)向’呢?也許他只是走快了一點(diǎn)而已。”直到晚年,他仍常常說起“螺旋式上升”這個(gè)概念。
“不這樣,會(huì)更寂寞”
熟悉卞之琳的人都說,他的晚年是寂寞的。
四川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比較文學(xué)教授趙毅衡是卞之琳在“文革”后招的首批研究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shí)他常去卞家,有時(shí)并不事先相約,但無論什么時(shí)候去,卞之琳都在家。
卞之琳是江蘇海門人,少小離家,卻保留了家鄉(xiāng)口音,旁人與他說話總像是隔了一層,能理解七八成已是不錯(cuò)。但趙毅衡覺得,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領(lǐng)域里,真正達(dá)到世界文學(xué)水準(zhǔn)的只有卞之琳的詩和張愛玲的小說。
周良沛那時(shí)在編《中國新詩庫》,為了“卞之琳卷”跑了多趟卞家。社科院宿舍樓像灰色的碉堡,卞之琳住頂層,別人家在搞裝修,卞家墻面上的石灰卻在脫落。
周良沛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去十次,九次都是卞之琳獨(dú)自在家。大書架把外面的光線擋了,白天也要開燈,他就在那里伏案寫作。門外街巷里熱熱鬧鬧,門內(nèi)卻像是古代寒窗苦讀的人,是舊版線裝書里的故事。
寫詩不成了,譯注工作也收了攤,卞之琳晚年主要在整理自己過往的著作。
訪美回來寫的詩歌發(fā)表沒幾天,他已經(jīng)開始修改其中的字詞。自選自編20世紀(jì)30年代的詩歌,他仍在琢磨哪里能刪一兩個(gè)字、哪里添上一兩個(gè)字,以符合他的格律主張。他曾給周良沛寫信,懇求其饒了他,別把他的某個(gè)作品收入選集。
他對(duì)于詩歌的解釋也有固執(zhí)的看法。一次,周良沛說起《斷章》讓自己理解了各色事態(tài)皆為風(fēng)景,卞之琳糾正他:“它只是表述一種相對(duì)、平衡的觀念,絕不可做別的推想。”周良沛想,作品寫出來,對(duì)詩歌的再創(chuàng)造就交給讀者了,豈是作者能統(tǒng)一得了的?作者如果因此產(chǎn)生不被理解的難堪,那未免活得太累了,這份完美太遙遠(yuǎn),追求的人注定是寂寞的。
社科院外文所后輩去看望卞之琳,回來說起一個(gè)發(fā)現(xiàn):卞之琳喜歡吃炸馬鈴薯片,聽它咬碎時(shí)發(fā)出的響聲。
能懂他的人日漸凋零。他曾與北大同學(xué)李廣田、何其芳共同出版《漢園集》,在20世紀(jì)30年代的詩壇引起轟動(dòng),“漢園三詩人”的名號(hào)因此得來。他們無所不談,尤其愛聊散文。
他的學(xué)生、后來成為圣路易華盛頓大學(xué)教授的裘小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卞之琳曾不無感慨地對(duì)他說,何其芳投身革命,李廣田成為大學(xué)校長,自己則是以翻譯為主,詩歌創(chuàng)作這條路實(shí)在是很難走下去的。
卞之琳喜歡給老友馮至打電話,多的時(shí)候一天兩三次,每次都聊很久。他的耳朵不靈,馮至說話聲音必須很大,掛了電話往往疲憊又感傷。
馮至曾告訴別人,卞之琳耳朵聽不清,總是自說自話,也許他太寂寞了,但不這樣,會(huì)更寂寞。
卞之琳80歲那年,他執(zhí)教西南聯(lián)大時(shí)的學(xué)生袁可嘉、杜運(yùn)燮、巫寧坤編輯策劃了《卞之琳與詩藝術(shù)》一書,為他賀壽。馮至為他的生日賦詩一首:不管命運(yùn)怎樣戲弄你的盆舟,你的詩是逆水迎風(fēng)的檣櫓……不必獨(dú)上高樓翻閱現(xiàn)代文學(xué)史,這星座不顯赫,卻含蓄著獨(dú)特的光輝。

十年后,袁可嘉、杜運(yùn)燮、巫寧坤再次發(fā)起卞之琳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為恩師賀壽。
袁可嘉從美國抱病前來,下飛機(jī)后卻聽說,卞之琳在當(dāng)天上午去世了。這天正是他農(nóng)歷90歲生日。
原定的會(huì)議如期召開,只是賀壽人都成了送行人。卞之琳喜愛白玫瑰,袁可嘉將兩朵白玫瑰輕輕放在他的胸前,俯身喃喃許久。
周良沛想,卞之琳是被推入歷史的深山古剎隱居的人,離開也是一種平靜。他常想起卞之琳坐在家中書房的樣子,窗外是北京冬春的風(fēng)沙,卞之琳安靜地坐著,是寂寞的,但也自享思想的富有。(完)

東西問精選:
- 2025年04月21日 21:20:12
- 2025年04月19日 20:32:13
- 2025年04月14日 21:19:00
- 2025年04月11日 20:42:12
- 2025年04月11日 18:2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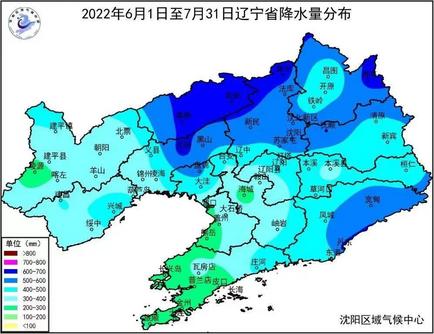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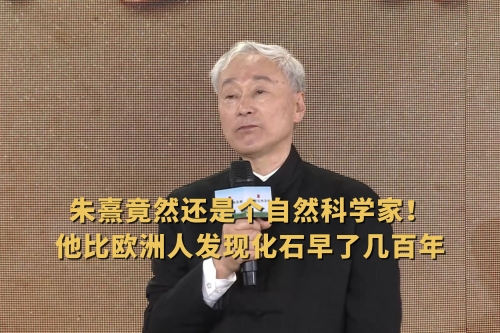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202009201號(hào)
京公網(wǎng)安備 11010202009201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