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劉海濱:梁啟超與衛禮賢為何堪稱東西文化整合“雙生子”?
中新社北京8月10日電 題:梁啟超與衛禮賢為何堪稱東西文化整合“雙生子”?
作者 劉海濱 上海古籍出版社哲學編輯室主任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擺在人類面前的,一面是生態環境問題導致的深層危機;一面是科技飛躍性突破帶來的難題。對此,需要人類智慧全力以赴,東西文化深入交流、整合,乃至發生新的躍遷,這是時代的呼喚。
所幸的是,伴隨著先覺者對現代性問題的深入反思,東西文化整合之旅在20世紀初已起步。梁啟超與衛禮賢(Richard Wilhelm)作為文化經歷者、體驗者,一由東向西,一自西徂東,兩人如同肩負同樣使命的“雙生子”,打開了東西文化整合的通道。
返本開新之道
戊戌變法失敗后,旅居日本的梁啟超于1903年遠渡美國,為的是聯絡海外華人尋求贊助,當然也想到冉冉升起的“新羅馬帝國”一探究竟。旅途所見,他一面痛心于華人社會的停滯不前,同時一把號準了現代化過程中的病癥:物質生活片面發展,精神生活貧乏枯竭——人類文明有墮坑落塹之虞。這個認識猶如囊中之錐脫穎而出,確立了其立足本國精神根基、整合東西文化的為學宗旨。
1918年底,梁啟超一行數人到歐洲考察。彼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硝煙未散,到處充滿著幻滅的氣氛。文藝復興以來一路高歌猛進的現代西方,遭遇了第一次重創。慕尼黑的中學教師斯賓格勒出版了一本書,名為《西方的沒落》,立刻引起巨大反響。歐美文化精英們慨嘆:現代文明到了重新調整方向的時刻。
1919年秋冬之際,梁啟超在巴黎郊外的寓所寫作《歐游心影錄》,系統總結了他關于東西文化整合的思想:立足中國傳統的修身之道,返回人類精神之本,開出適應現代需求之用——此之謂“返本開新”,正是其基于對現代性的深刻認識提出的中國文化復興之路。

溝通中西之路
與梁啟超同時,一位西方學者正肩負著同樣的歷史使命。1873年5月10日,衛禮賢出生于德國斯圖加特,只比梁啟超晚了兩個多月。1899年作為傳教士的衛禮賢來到其時作為德國租借地的青島,對中國文化一見鐘情,此后20年一直待在中國。他通過興辦學校,結識了一批精通舊學的學者,特別是1911年之后前清遺老及各界文化人士紛紛來到青島避難,衛禮賢與他們一道組織“尊孔文社”,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學習環境。一同參與交流活動的,還有在青島旅居的德國學者,他們經常開展東西方對話,故又稱“中西文社”。再加上隨后興起的經典翻譯,這些活動成為衛禮賢深入學習中國文化非常有效的方式。到1920年前后,衛禮賢已是蜚聲中外的翻譯家和漢學家。
值得關注的是衛禮賢與勞乃宣合作翻譯《易經》的經過。曾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學部副大臣的勞乃宣,不僅傳統學養深厚,對于世界形勢、各國政治也非常了解,還精通數學和音韻學,積極推行漢字簡化和拼音。1913年,由前山東巡撫周馥鄭重引薦,衛禮賢成了其時已逾七旬的勞乃宣的正式弟子。勞乃宣詳細講解《易經》的文句義理,衛禮賢在理解消化的基礎上逐句譯成德文,為防止遺漏和偏差,再回譯成中文,請勞乃宣校正。在此期間衛禮賢陸續翻譯出版了《論語》《老子》《列子》《莊子》《孟子》《大學》等經典,《易經》的傳習和翻譯則歷時數年,至1921年終于完成。1924年衛禮賢應法蘭克福大學之聘回國,同年《易經》德文本出版,隨后被轉譯成各種文字,傳遍整個西方世界。
衛禮賢的文風與梁啟超相似,其翻譯的中國經典并不強調文句層面忠實原著,而是把握其精神主旨,以生活化的語言疏通大意,因而大受歡迎。除了儒道經典,他還選譯《三國演義》《聊齋》等通俗文學,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的文章。同梁啟超一樣,衛禮賢溝通中西,乃是立足當下,面向未來;通過他的翻譯和著述,不僅力圖呈現給西方一幅完整的中國文化圖像,更通過這些表象傳達活潑的中國文化精神,進而激活與拓展西方文化。可以說,德語世界乃至整個西方經由衛禮賢的作品,對中國文化精神的了解逐漸深入。

文化體驗之旅
與一般人眼中的“做事業”不同,衛禮賢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認同植根于自身體驗,是自我生命成長的需要。他把與中國相遇看成一種天命,以自身生命感知中國人的心靈,乃至與往圣先賢精神相通。
中國文化的學習,反過來又促進了他對西方文化的體認。一戰結束時,衛禮賢為家人和羈押在青島的德國戰俘寫過一本小書——《耶穌其人》。與常規的《圣經》解釋不同,衛禮賢將耶穌看成不斷走向徹底澄明之境的“修成”的圣者;換言之,將“道成肉身”轉換為東方讀者熟悉的“肉身成道”。這當然與衛禮賢汲取東方文化有關,但并不能簡單看成是東方思想的移植,而是借由東方觸發西方宗教豐富的靈性資源,就如經由佛教東傳,儒學開出了宋明理學,既不能否認佛教的激發作用,也不能簡單認為是儒學的借用或變異。
衛禮賢立足于求道之志和心靈體驗,其文化溝通達致精神超越的層面。1925年,衛禮賢在法蘭克福大學創辦中國學社,在成立儀式上作了題為《東方和西方》的發言,概括了對中國學社的期望,亦即自己的文化使命。他指出,中國學社旨在連接東西方的精神,不能停留在表面,而須追問中國及東方根植的最深層力量。
對此,梁啟超與衛禮賢二人共同的好友張君勱看得清楚,指出“衛禮賢不是文化研究者,而是一個文化經歷者,一個文化領會者”。二者的區別在于方式不同,一為外在考察,一為內在體驗。文化經歷者是從個體生命需求出發,尋求自我精神困境的解決之道,以此為基礎推己及人,再推廣到整個時代;而文化研究者是從所謂客觀(外在于自我生命)的問題出發,與自我的生命體驗是隔離的。
同樣,梁啟超也是個文化體驗者。依據自己的修身體驗,梁啟超拈出王陽明和大乘佛教。“大乘”指的是佛教究竟圓融的意旨,其特質是世俗生活和超世精神圓融為一,佛教的發展可看作是此宗旨不斷開顯的過程。實則這也是中國文化精神的體現,馮友蘭用儒家的語言概括為“極高明而道中庸”。一方面,儒釋道三教通過互相激發,在各自內部不斷趨近之或完善表現之;就文化整體而言,至少從唐宋以來,三教融合為中國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其內在理路即是不斷趨近此真精神。王陽明的“致良知”教法,從儒家內部發展來說相當于儒家的“大乘”,就中國文化而言,則可看作三教融合的成果,其特點是每個人就各自職業和身份的方便,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修煉精神,被梁啟超認作適合現代人的“不二法門”。

共擔使命之友
1920年后,衛禮賢短暫回德國,1922年初以德國駐北京公使館科學參贊的身份再來中國,1923年受蔡元培禮聘在北京大學教授德國文學,同時創辦“東方學社”,在此期間與梁啟超、胡適、張君勱、徐志摩等來往密切,結為摯友。
衛禮賢對梁啟超十分推崇,不但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援引和轉述梁啟超的思想,還在中西互釋的語境中與之唱和,例如在將梁啟超所作《佛教心理學淺測》翻譯成德文的同時,自己又寫了一篇續文加以引申闡發,甚至還向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推薦梁啟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走完高度神似的人生道路之后,兩人差不多同時離世。梁啟超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去世;不久衛禮賢也突然舊疾發作,于1930年3月1日在德國圖林根病逝。兩人僅得中壽的一生,因異常勤奮和精力充沛,各自留下了數量驚人的著作,分別在東西方取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梁啟超與衛禮賢作為肩負同樣使命的“雙生子”,打開了東西文化整合的通道。正如梁啟超返本開新的道路為后來的現代“新儒家”們所繼承,衛禮賢的經典新譯和中西互釋路徑也為后繼者開啟了一片新天地。(完)
受訪者簡介:

劉海濱,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哲學編輯室主任,副編審。長期致力于傳統文化和古典學術的研習和傳播,主編《原學》輯刊,出版專著《焦竑與晚明會通思潮》、編選《熊十力論學書札》等,策劃出版的重要圖書有“新編儒林典要”叢書、“佛門典要”叢書、“中華家訓導讀譯注叢書”、《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梁啟超談家庭教育》《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場講演》等。

國內新聞精選:
- 2024年12月22日 17:59:03
- 2024年12月22日 16:48:36
- 2024年12月22日 15:53:01
- 2024年12月22日 09:16:06
- 2024年12月22日 09:08:46
- 2024年12月21日 19:19:45
- 2024年12月21日 17:09:19
- 2024年12月21日 14:25:07
- 2024年12月21日 11:25:59
- 2024年12月21日 10:59: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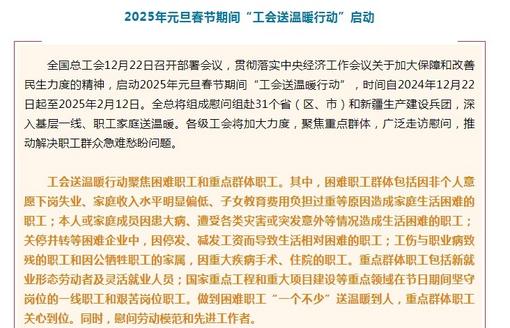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20200920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