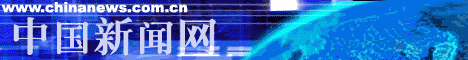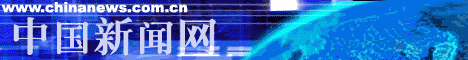(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wù)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并注明摘自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周刊》。聯(lián)系電話:68994602)
艷遇大如牛
瞿塘峽江心橫著一塊石頭,叫滟滪堆。船只與石頭的碰撞,那絕對是最可怕的艷遇了。劉白羽的《長江三日》就記錄了當(dāng)?shù)卮さ囊痪漤樋诹铮轰贉笕缗#奶敛豢捎巍D菚r我們剛知道所謂艷遇,就是一男一女有一段曖昧?xí)r光,一個師兄將船工的順口溜略作修改,成了“艷遇大如牛”。
男人都渴望艷遇。據(jù)說最容易發(fā)生艷遇的場所是火車或輪船。按我的理解,這種動輒需要耗上幾小時乃至十幾小時的工業(yè)革命時代的產(chǎn)物,要是一男一女比鄰而坐,他們之間發(fā)生點艷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基于這種認(rèn)識,我的一位42歲仍然未婚的哥們兒,總是在所有節(jié)假日去遠(yuǎn)行,其意不在于風(fēng)景,而在于艷遇。據(jù)說有幾次他差那么一點就成功了,可最后還是一個人孤獨地回來。這家伙有天喝醉了酒,十分真誠地問我:“你說我算不算鉆石王老五?”我差點笑得背過氣去:我認(rèn)為,你他媽至少算是磚頭王老五。
磚頭王老五心地善良,我常祝愿他能早日有艷遇,他也在自身條件方面狠下功夫,為艷遇時刻準(zhǔn)備著。他本是某廠的工會干部,天天過著呆板的日子,這自然與艷遇的要求格格不入。于是在讀完《廊橋遺夢》后,他花盡積蓄買了一臺專業(yè)相機(jī),到了他拍下來的照片基本能分清男女老少時,他就像一條在春天里幡然醒悟的水蛇那樣上了路。
磚頭王老五的艷遇至今仍沒有發(fā)生,勉強(qiáng)稱得上準(zhǔn)艷遇的倒有兩起:
其一,成都有家酒吧,男女顧客可以互相寫紙條,由服務(wù)生將它們折成紙鶴傳遞。我的朋友是這家酒吧的常客,常常被要求獨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國》什么的。還是得承認(rèn),我的這位朋友很有音樂天賦,有天他唱完歌,服務(wù)生送來一張女人的雞毛信。當(dāng)我可憐的朋友興沖沖地前去與女主角見面時,他捂住臉尖叫著跑了回來:那位邀請他加入艷遇游戲的女人完全可以做他慈祥的祖母。
其二,一個重慶女編輯到成都組稿,我請她吃飯。磚頭王老五聽說有美女,吵著要作陪。一頓飯下來,磚頭王老王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告訴我他已經(jīng)愛上了美女編輯。于是我慫恿他說,你到美女編輯窗下為她唱歌吧,如果她一感動,你的艷遇工程不就大功告成了嗎?我可憐的朋友一身酒氣去了賓館,從《我和我的祖國》唱到意大利人聽不懂、中國人更聽不懂的《我的太陽》。唱著唱著,憤怒的美女編輯撥打了110。
經(jīng)歷了這么些挫折,磚頭王老五還不死心,他至今仍在努力尋找艷遇。他堅信,既然有了艷遇的愛好,又肯鉆研,咱中國這么大,美女這么多,還怕沒有艷遇在前方等著嗎?所以,艷遇的前途是光明的,雖然道路有些曲折。
文/聶作平
深圳女人的現(xiàn)實與夢想
大約一年前,朋友從順德來深圳公干,閑來無事找了家網(wǎng)吧與人聊天。網(wǎng)友是個深圳女孩,兩人聊得很投機(jī),而且,相問之下,他們竟在同一家網(wǎng)吧。于是互留了手機(jī)號碼,約好門外碰頭,一起去喝茶。見了面,問候寒暄——女孩子一直在看他,相貌普通,也不像有錢人,突然說:“算了,太晚了,我想回去了。”朋友問,要不要送?女孩說,不要。朋友便自去拿了車鑰匙開門——他是駕車來的,還是白色寶馬。剛開出不遠(yuǎn),手機(jī)響了,那女孩說她等不上車,想蹭車回家。
朋友說,深圳女人太現(xiàn)實,我無法否認(rèn)。若說深圳女人有什么共性,首先就是“現(xiàn)實”,盡管她們來自全國各地,本事運氣各不相同。這是環(huán)境所致,深圳根本就是一個現(xiàn)實的城市,十足的商業(yè)氛圍、競爭的壓力、背井離鄉(xiāng)、漂如浮萍——如果還有什么可以信任和依靠,那應(yīng)該就是物質(zhì),就是錢——我相信很少有女人一開始就這樣想,一開始就愛鈔票多于玫瑰,是現(xiàn)實教給她們的。
若真的只是現(xiàn)實也還好了,但是,我發(fā)現(xiàn)——正是因為太現(xiàn)實了,深圳女人心里的夢想也特別強(qiáng)烈,那是對愛的夢想,幾乎到了熱切的地步,可惜多是無奈,甚至悲劇——如果你留心過電臺夜間那些談話節(jié)目,還有報紙上的情感專版,滿是怨訴:孤獨的女強(qiáng)人、糊涂迷陷的年輕女孩,還有那種一直以來專心做著老婆,一不留神卻遭人拋棄……所以我有時想,深圳或許不是一個適合女人生存的地方,或者,深圳的女人,是要離傳統(tǒng)的幸福遠(yuǎn)一點的。一切都要有代價,高薪有代價,比如,推遲結(jié)婚與生育,遠(yuǎn)離恬淡安然;可以自由地享受性也有代價,比如,不被承諾,隨時準(zhǔn)備接受各種后果。但也許我說的根本不對,不然為什么這城市里還活躍著那么多女人,而且外面的女人還是源源不斷涌來?滿街都是女人,酒樓茶樓里,自己組織相聚自己買單的女人,連播放足球賽的酒吧里晃蕩的也盡是吊帶背心的身影。
女人的潛能是很大的,越是活躍、開放的地方,她們越適應(yīng)——比男人更能適應(yīng)。深圳也的確有很多看起來活得成功而漂亮的女性,一切都有代價,但也有所得到,到底是好是不好,誰又能說得清?
文/朱碧
床比房子更重要
搬進(jìn)新家后,我那張真皮大紅圓床,一直是眾女友談?wù)摰脑掝}。她們都覺得,對單身而言,這張2.1米的大床很暴殄天物;但見過之后,又都忍不住要問,多少錢,在哪買的,有沒有別的顏色——一副要將自家的床徹底換掉的樣子。
接下來好幾個單身女友都搬進(jìn)了新家,卻沒有一個人真正效顰——不是說臥室太小,就是說那種床實在太張狂,怕和房子不配。
我很得意。自己的小房子,落下這么一張床,實在是有點驚世駭俗,不光價錢,造型、材質(zhì)和體積,統(tǒng)統(tǒng)不合常規(guī):一張床就占去大半個房間,剩下的只夠放一個衣柜;大紅的皮子,香艷而狂放,雖然依舊是孤枕的下場——我還是很得意地翹著鼻子,夜夜在我的大床上,睡到每天上班都要遲到。
我到一個朋友的豪宅去看過,樣樣都很考究,光書房就兩間,他和太太各不干涉,主臥也大——但那張床,他得意地告訴我,才花了700元,在家具批發(fā)市場侃價買的——而他的房子,花了70萬,他的沙發(fā),花了7000,他的一個根雕,花了2000——他樣樣都炫耀,包括他的床,他覺得撿了天大便宜的床。本來我是很嫉妒的,因為他住的是190平米的復(fù)式,而我住的還不到70平米,但他那張床平息了我的嫉妒,我立刻又翹起了我的鼻子,覺得自己活得比他有素質(zhì)。
床多重要啊,在家里,它是我最喜歡呆的地方,臥讀、按摩、練瑜伽、做愛,當(dāng)然還有我至愛的睡眠。我無法理解和我那個朋友類似的某些人,買一套極豪華的沙發(fā),讓客人贊美,自己的內(nèi)心得到滿足;而對與自己最貼心的床,卻極度湊合,反正別人也看不見,多花的錢,都是冤枉。就像某些看起來時尚的女子,講究品牌,講究配飾,卻月月去地攤買內(nèi)衣——真難想象,如果某個為她光鮮衣裝傾倒的男人,在兩情相悅的某個春夜脫下她的華服,看到那兩件明顯來自地攤的內(nèi)衣,會不會從此失了激情?
還認(rèn)識一個剛畢業(yè)的小女孩,分到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買了一張雙人床,雖然她至今還沒男友,但她說,一個人也可以睡雙人床啊,多舒服啊。我差點擁抱了她。是的,一個人睡雙人床的感覺,或許就是你獨立生活的坐標(biāo),我們不要有人分享,我們?yōu)樽约贺?fù)責(zé)。
當(dāng)愛情和房子都還沒有來臨,至少我們有足以支付一張床的能力,愛情和房子,或需要緣分,或需要金錢積累,但是床不,并且,我們的夢想,多半誕生在床上。如果它足夠柔軟,足夠?qū)挻螅銐驕嘏敲次覀兊拿魈欤銜谐渥愕牧α咳崿F(xiàn)夢想。
文/曾敏兒
男人的臂長等于女人的腰圍嗎
“男人的臂長等于女人的腰圍嗎?”
如果這話是男人對女人說的,那他一定是個準(zhǔn)備探索愛情未知領(lǐng)域的勇士,為了說出這話,他經(jīng)過了長期跋涉——諸如送玫瑰花、陪著逛街等。在某個春風(fēng)沉醉的傍晚,他突然間問出這么句話,神色認(rèn)真得仿佛在探討一個前沿的科學(xué)課題。然后,男人的臂膀便作圈套狀圍了過去。明知是個美麗的陷阱,女人也心甘情愿墜入,任由男人來測量她的婀娜身姿。
如果這話是女人對男人說的,那她一定是個愛上了一塊木頭的男人,為了說出這話,她經(jīng)過了長期的心理斗爭——諸如暗送秋波、輾轉(zhuǎn)試探等。在某個談興正濃的夜晚,她突然間問出這么句話,神色迷惑得仿佛解不開的金字塔之謎,他沒理由不把那只一直揣在褲兜里的手掏出來了。于是,女人不偏不倚地倒在了男人恍然大悟的臂彎里,結(jié)果是,靦腆的男人找到了如山的豪氣,而女人則比買到一件合身的套裝還高興。
男人的臂彎圈進(jìn)女人腰身的瞬間,是個類似于發(fā)電廠開始工作的過程。被電流擊中的男女往往會忘了他們剛才探討的是什么問題,管它呢,這個問題留給有游標(biāo)卡尺的物理老師去研究吧。事實上,不管有多大誤差,他們都認(rèn)定了他的臂長就等于她的腰圍。
男人的手臂摟住女人的腰,直到摟著走上紅地毯。當(dāng)他們開始了“圍城”里的生活,女人覺得男人的臂彎變成了“緊箍咒”,男人開始覺得女人的腰身變作了個“火藥桶”,世界上便有了“離婚”這個詞。還有些人可以一直幸福地相摟,一年,十年,二十年……男人的臂長恐怕是這輩子再也不會增長了,可女人的腰圍卻會有所改變。但男人的手臂總能很合適地攬在了女人的腰上。女人懷孕了,腰身啤酒桶般粗起來,這時男人會如抱著個價值連城的古董般小心;等到女人老了,男人的手臂也枯萎無力了,這時女人和男人異口同聲地問:“男人的臂長等于女人的腰圍嗎?”答案將是四行渾濁的眼淚……
這個古老的問題,不知是什么時候提出的,也不知有多少男女努力解答過,也許一直都沒找到答案,也許是知道了的人不想說——好給人們留下一個浪漫的愛情誘餌。
文/元明清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