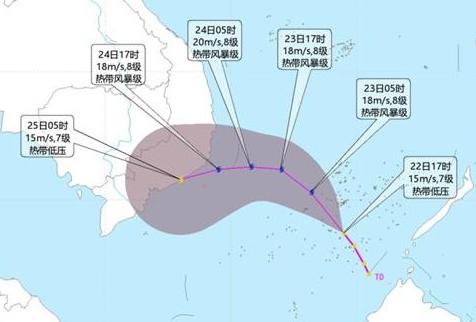被卡路里支配的進食障礙患者:體重24公斤還不瘦?
 參與互動
參與互動從吃不飽飯,到吃不下飯——
被卡路里支配的人
瘦是有止境的,對瘦的渴望沒有。
最瘦的時候,身高148厘米,體重24公斤,身體像根“火柴桿”,盧佳羽還是覺得自己不夠瘦。
過去3年里,北京的這位中學生通過節食瘦了30多斤。“消瘦”不足以形容她。因為攝入脂肪過少,影響了雌激素的合成,她停過月經。
她對進食這件事斤斤計較。某種刻板程序遙控了她的進食:她需要在固定的時間進餐,一頓飯能吃一個小時;碗盤要按固定順序擺放;水果要切成指甲大小;米飯幾乎是一粒一粒咽下。她列過一份不容出錯的食譜,打印后貼在墻上,家里請過2個阿姨最后都選擇了辭職。她為了控制煮雞蛋的時間而購買了計時器。家人給她的杯子里加多了牛奶,也會導致她的大喊大叫。就連在課堂上,她也常常為計算卡路里而走神。
這種狀況在2016年——她13歲時出現。第二年,母親在社交網絡描述了她的情況,有人提醒要去就醫。她確診了。
官方定義是“進食障礙”。這個孩子符合醫生對進食障礙基本特征的描述:進食行為異常,對食物和體重、體型過度關注,多發于年輕女性——根據醫學文獻,女性與男性患者的比例超過了10∶1。這是精神疾病的一種。
常人對它幾近無知。在2019年3月之前,百度百科詞條里,進食障礙還被列為消化內科疾病,主要癥狀被描述為,“營養不良,消化道及內分泌癥狀”。
中華醫學會心身醫學分會進食障礙學組副組長、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綜合三科病房主任李雪霓作為專家參與了詞條的修改工作。更新后的版本是:“精神科疾病,由個體因素、家庭因素及社會文化因素造成”。
少為人知的事實是,厭食癥是精神科致死率最高的病種。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就此采訪的多位醫學專家都強調,根據全球已有的研究,其致死率高達5%至20%。
北京的另一位患者的母親記得,女兒去美國讀大學3個月后,體重降了10斤,半年后又掉了9斤。這是一位體型正常的年輕女孩,在18歲成人禮上還穿著小號禮服走過紅地毯。等到假期回國,她整個人“縮了好幾圈”。
女兒開學去美國之前,與心理咨詢師約定了一個很實際的目標:“活著回來。”
1
醫生李雪霓見過不少進食障礙患者的死去。她所在的北大六院,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是國內最早治療進食障礙的醫院。
進食障礙本身并不致死,但過度消瘦會引起心律失常、器官衰竭,進而導致壽命縮短。通常情況下,患者會產生抑郁情緒。有人死于自殺。
李雪霓看到,因為進食障礙,有的病人命懸一線,住進了重癥監護病房。她記得,一位病人經過治療,剛恢復規律飲食,但身體機能突然崩塌,轉到綜合醫院搶救了一個多月。還有人死在住院前一天的夜里。
這位醫生見過的病人里,有的是被人用平車推進來的,有的插著鼻飼管,或者就診時已全身水腫。
據李雪霓介紹,按照醫學論文公開報道的情況,進食障礙群體有個“四分之一”定律:不干預的話,1/4的人可以自行痊愈;1/4的人會好轉,帶著癥狀正常生活;1/4的人患病慢性化,生活受到影響;1/4可能會死掉。
著名醫學期刊英國《柳葉刀》雜志2016年刊發的一篇論文估計,歐盟大概有2000萬進食障礙患者。中國尚缺乏相關研究數據。
過去很多年里,醫學界沒人認為中國存在進食障礙這種疾病。
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一種說法是,“進食障礙只見于西方”。這種假設陸續被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香港等地報告的病例推翻。
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有西方學者仍主張中國不存在進食障礙患者,北大六院醫生張大榮把她的兩位患者帶到了會場,改變了人們的看法。
不過,2002年之前,北大六院的進食障礙治療基本局限于門診。在張大榮的帶領下,該院于2011年建立了國內最早收治進食障礙患者的專科病房,她也被稱為中國進食障礙治療領域第一人,擔任了中華醫學會心身醫學分會進食障礙學組榮譽組長。
1987年,中國大陸幾乎沒人聽說過進食障礙時,張大榮的導師、精神病學家沈漁邨就提出,這將是未來中國的一個嚴重問題。
沈漁邨后來成為中國精神病學領域的第一位院士,她的預言已經部分成真。
北大六院綜合三科統計,2002年到2012年,該院住院的進食障礙患者從年均20余例增長至180余例。開了專科病房之后,李雪霓曾以為會缺乏病源,可一段時間后,發現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統計數據也顯示,進食障礙患者數迅速增長,2002年該中心門診僅收治3例,2018年是591例,患者來源地從一二線城市向三四線城市“拓展”。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心身病房主任、進食障礙診治中心負責人陳玨說,進食障礙曾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在中世紀就有關于自我絕食的記載。自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文化“以瘦為美”之風愈演愈烈,進食障礙的發病率也逐年上升。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還沒完全解決溫飽問題,加上傳統文化中孩子以胖為美的觀念,進食障礙在當時的中國并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然而今天,溫飽問題解決后,人們吃飽了飯,進食障礙又多了。
2
吃不下飯的風險,很多人意識不到。
最瘦的時候,盧佳羽肋骨根根分明,后背骨節清晰可見,臉色蠟黃,頭發干枯、掉落。有人形容她“瘦得就像筷子似的,一碰可能就折了”。她身體容易發冷,冬天在開了熱風的房間,即使蓋了兩床被子,還是感到冷。
另一位患有進食障礙的學生描述,走路時,她總感覺腳懸著沒著地,好像一陣風都能把自己吹倒。教室外一排柜子的柜門反彈力度有點大,她曾被彈倒在地。
北京協和醫院臨床營養科副主任陳偉為不少進食障礙患者做過胃鏡,他見過的胃壁,有的跟“一張紙一樣,幾乎要破掉”。
進食障礙主要分為厭食癥和貪食癥。貪食癥患者會出現反復發作、不可控制的暴食,并在暴食后采取誘導嘔吐等代償行為,避免體重增加。因為暴食,胃會被一點點撐大,胃壁也越來越薄。
1994年,陳偉接診了一位30歲的已婚女性,她身高165厘米,體重只有29公斤。醫學檢查排除了器質性疾病的可能。根據消化內科醫生的提示,他第一次關注到進食障礙。
據陳偉介紹,在北京協和醫院臨床營養科的進食障礙患者,最早一年只有一二十人,可近10年每年都在百人左右。他還注意到,患者越來越低齡化,時間跨度變大,病情也越來越重。他見過,一個初中班里幾個女生扎堆兒來看病。
陳偉認為,進食障礙由于多發于青少年成長發育期,對人的影響十分多元。直接的反應是,厭食癥患者因為長期不吃東西,胃腸排空能力變差。他解釋,瘦到一定程度后,人體產生“保護措施”,食物不會被快速消耗,有的患者48小時前吃下的東西還停留在胃里。
這位營養科醫生指出,人體的許多功能能夠跟隨營養狀況動態變化,但這些患者即使營養恢復,“仍有一些機能無法恢復到之前的健康水平”。
這些人或多或少地伴有便秘、脫發、失眠、骨質疏松、卵巢早衰等癥狀。長期營養不足,神經元的功能受到影響,也會造成精神抑郁、注意力難以集中等情況出現。
也正是因為便秘、失眠等并發癥,進食障礙經常隱身在其他病癥后面。李雪霓說,多數患者一開始找到的是營養科、消化科,或者內分泌科、婦科。他們會抱著烏雞白鳳丸、加味逍遙丸之類的藥物走出醫院,或者按要求調理一段時間,藥沒少吃,病癥仍在。
一個問題是,一些進食障礙的病情危急患者常常夾在“中間地帶”:精神科認為指標太危險,希望患者能先去綜合醫院做生命支持的處理和監護;可綜合醫院診斷后表示,這是自己餓的、吐的,應該去精神科。一位患者在消化科確診了厭食癥,但病歷上“治療意見”一欄是空的——很多其他專業的醫生不知道怎么治療。
擁有幾十萬名粉絲的“吃播”主播尹璇,患有進食障礙6年。她主動去醫院檢查時,拿到的結果顯示,只有一個指標不太合格,“好像沒什么大問題”。
李雪霓不否認這個說法,在她的經驗里,進食障礙患者在前期檢查時被發現的頂多是“心動過緩”。一般情況下,由于不了解實際情況,醫生往往會下個不痛不癢的結論:“最近老不運動吧”“只是比較瘦造成的”,最后落到一句,“你得加強營養”。
3
即使是現在,進食障礙的確切病因也是未知的。一個共識是,生病的前提是極端減肥行為和個人、家庭、社會因素碰在了一起。
在陳玨的印象里,來到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不少進食障礙患者家境優渥,本人也挺優秀,“至少看上去已經很完美了”。
但這些患者不這么認為。其中一位在社交網站上這樣填寫個人簡介:“一個正在變成廢物的人”。
觸發疾病的導火索多種各樣,但所有的厭食癥患者都有相同的根本原因——完美主義以及低自尊人格。李雪霓總結,進食障礙的患者普遍特別敏感,對于挫折的耐受度較低,會盡其所能避免傷害的發生。也只有控制食物的時候,他們才會找到丟失的安全感。
34歲的程一喬,學業優秀,曾任教于北京一所知名中學,擁有小蠻腰、“馬甲線”和6塊腹肌。她13歲那年患厭食癥,記得自己瘦到“只剩一把骨頭”,還在腿上綁著沙袋,在操場上一圈圈跑步。
告別進食障礙快20年了,她感覺它沒有完全離開,“更準確的說法是帶病生活。”
直到現在,她仍然討厭自己的身體——大腿還是太粗,腰可以更細。后來她反思,之所以對自己痛下“狠手”,是因為內心里從沒接納過自己真實的樣子。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瘦是好看的。”她說,自己想要認可,瘦下去就是最保險也最簡單的方式,“厭食癥是這些心病最末端的癥狀,也是各種問題的集合。”
盧佳羽小時候,父母先是分居,后來離婚,她跟著母親從國外回到中國,頻繁地搬家,換學校。她覺得“交朋友是世界上最難的事”。為了掩飾尷尬,一個人在學校食堂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午飯,之后就在教學樓繞圈打發時間。她成績突出,當過辯論賽的最佳辯手,也曾在舞蹈大賽里斬獲亞軍,她同時抑制不住自己要去“討人喜歡”。
李雪霓醫生形容,就像是“一個個鎖扣都扣在一起了”,要全部解開是件麻煩事。治病的同時,還得治人。
關于發病機理,一位患者稱,就像是“先天的基因給槍上好了膛,而后天的環境扣動了扳機”。
對盧佳羽來說,減肥是一切的開端。她13歲那年生了一場大病,服用激素藥物,看著自己的臉“像饅頭一樣發起來了”。
她的想法是:只要瘦下來,一切都會變好的。
此后她視高熱量為敵人。1千卡等于4.186千焦,她把卡路里對照表背得滾瓜爛熟。為了減少攝入油脂,這個少女告別了生日蛋糕和蘋果派。
一般來說,人體BMI指數低于18.5屬于過低,低于13就是高危。盧佳羽的BMI指數最低時只有11,令她的母親憂心忡忡,因為很多醫院不敢接收BMI低于13的患者。
盧佳羽記得,體重秤上遞減的數字帶來過成就感。家人覺得她有驚人的自制力,朋友的夸獎接踵而至。
但是,因變瘦而來的贊美很快消失了。夸過她的朋友再評論她時,用的是“尖嘴猴腮”。
她吃飯的緩慢也變得“全年級有名”。和同學一起用餐時,她會偷偷把肥肉和主食塞在餐巾紙底下,假裝自己吃了。
在進食障礙支配下,這些患者千方百計地與食物“捉迷藏”:找借口逃避進食,聚餐時把盤里的食物藏起來,或是干脆服用瀉藥。用盧佳羽的話來說,就像是戴上了一個“緊箍”,被迫與食物捆在一起,再無法思考更重要的事。
部分社交也被阻斷——在以聚餐形式組織起來的聚會上,他們沒法坦然自若地交談。
有人甚至從家庭餐桌上退出,躲進自己的房間吃飯。在這些家庭里,圍繞著吃飯產生的問題層出不窮:有人無法控制自己,經常摔東西罵人;有的患者自己吃不下去,喜歡看別人吃飯來“望梅止渴”,一位疼愛女兒的父親因此連吃了5個饅頭,等到第六個真的吃不下了,只能藏在褲兜里。
“為什么不吃飯?”這是厭食癥患者被問到最多的一個問題。其實,他們并不像這種疾病名稱的字面意義那樣“厭惡”食物。很多人都曾在網上搜索過一些高熱量的食物圖片,將圖片一張張劃過,常常一看就是一下午,隔著屏幕“吸收養分”;有人的直播平臺賬號關注列表里,是一連串的“吃播”主播。
盧佳羽的母親林樺與不少患者打過交道。她發現,在厭食癥人群中,大家反而紛紛以“吃貨”自居,喜歡在微信朋友圈里曬出美食圖片。這些在相對富足的年代殫精竭慮差點把自己餓死的患者里,有人的理想職業是——廚師。
4
餓得時間太長,身體可能出現補償反應。在厭食路上,一部分人轉向了貪食——某一天突然把持不住,一口氣吃掉更多。由于那根對卡路里敏感的神經還繃著,最終只能選擇吐掉。
尹璇是在讀大學期間開始減肥的。厭食4年后,她又必須適應自己貪食癥患者的身份。吃飯時,她要避開人群頻頻去廁所。她的床下塞著垃圾袋和塑料桶,因為怕人發現,半夜兩三點是催吐時間。
貪食階段,不少人陷在“吃了吐、吐了吃”的循環里。很多名人都患過進食障礙,以演員和模特居多。據報道,美國歌星Lady Gaga從15歲開始,就在貪食癥及厭食癥間掙扎。
30歲的何一,第一次催吐是在18歲。那是年夜飯后,對著滿桌的零食,她打開了一包平日不敢碰的小餅干。一包,又一包。她感覺這些餅干正在變成腰間贅肉,去了廁所第一次催吐。
她感覺自己找到了一種“魚和熊掌可以兼得”的辦法,當夜又吃、吐了一輪。回到大學,她繼續節食,繼續健身,繼續催吐。吐的頻率從一兩周一次變成一天一次,有時甚至一天三次,“醒著時除了吃和吐,就是在計劃吃和吐”。有時,她會在嘔吐物里見到血絲。
她會被自己的瘋狂嚇到,比如她會把食物帶著包裝扔進垃圾桶,想吃的時候又從垃圾桶翻吃的。
催吐四五年后,她的身體也形成了一些病態的反應機制:牙齒擋不住胃酸的反復侵蝕,她有四顆臼齒是嚴重蛀牙。胃液會突然反流,突來的惡心感把她從睡眠中揪醒,她只能探頭吐在地板上。她感覺自己被對食物的恐懼淹沒。每吐完一場,喉嚨里連帶著整個食道充斥著燒灼感。
被喜歡的異性告白時,她滿腦子想的都是,“我還沒到完美的體重,應該去把晚上吃的全吐掉。”
厭食轉貪食后,尹璇參加“大胃王”比賽,并找到“用武之地”,成為“吃播”主播。她需要展示的,有些是商家要求“帶貨”的產品,比如成箱的罐頭。一次直播可能就要吃下將近20樣東西。父親幫她簽收過數不清的快遞,最多一天有十幾件,一個廠家有時就是一兩箱。
她白天睡覺,晚上的黃金時段,打開攝像頭,直播到午夜。同一屋檐下的父母知道,鏡頭之外,她會催吐好幾次。
為了催吐,她的房間里放了很多的塑料桶,還有兩三箱大桶礦泉水。
在尹璇出門的時間里,父親才有機會進入她的房間,把堆滿食物的臥室收拾一下。
因為直播,她的生活被打亂了:原先是一日三餐再加些量,現在她吃得集中、吐得頻繁了。
父親擔憂她的身體,卻也怕摧毀她目前幾乎是僅有的成就感。因為堅持這件事,她的人生尚未失控。他擔心平衡點不可持續,“搖搖晃晃的,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塌了。”
爭論起來,尹璇會用一句話安慰他:“你放心,我比你掙得多。”
讓這位父親更擔憂的是,很多“吃播”視頻下面,知情的粉絲會打出一個“兔子”的表情,隱晦地表示催吐的含義。在電商平臺,要買到催吐工具毫不費力。他覺得后怕,“你根本躲不開現在的網絡環境”。
《2019淘寶美食直播趨勢報告》稱,美食直播成為淘寶吃貨經濟的“新風口”,僅2018年便有超過16億人次在淘寶“蹲守”美食直播。百度指數也顯示,2014年4月到2019年6月,“吃播”指數從幾近為0增長至近4000點。
一位擁有1000多萬微博粉絲的主播,一頓飯能吃下一只35斤的烤全羊或40碗獅子頭,早餐是100根油條和4碗胡辣湯,就連吃煎餅也是加30個雞蛋、5個肘子、5份芝士和5份雞肉。可鏡頭里的她瘦得讓人驚訝。
有的主播結束后沒關鏡頭去了衛生間,屏幕里傳來了嘔吐的聲音。
北大六院的志愿者老曹管理著不少進食障礙患者和家屬的微信群。他說,幾乎所有家屬都對這件事情“非常氣憤”,認為商家出于利益的考慮,忽視了潛在的社會風險。
尹璇的父親找過一家舉辦“大胃王”比賽的電商平臺,對方表示理解,態度很好,但回復是,“我們已經花了錢了,取消不了,可以在節目中適當加些‘請勿模仿’類的提示。”
5
與熱鬧的“吃播”相反,進食障礙處在一個冷清的角落。林樺記得,女兒患病后,她在網上搜索進食障礙、厭食癥、暴食癥這類關鍵詞,搜到的圖書寥寥無幾,“有的是20年前出版的,蓋著圖書館印章,買回來已經有霉味了”。
另一位母親曾試探著與別人談起女兒的病情,說了半天,對方并不理解,“這很嚴重嗎?不就是吃飯嗎?這還是個病?”
林樺是一位在公司最高管理層中的職業女性,她用部分時間研究心理學,考下了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證書,幫忙組織患者和家屬的活動和分享會,一些家長也找到她求助。有人心急火燎地咨詢,可聊了半天,只會反反復復地問,我孩子到底該怎么辦?
陳玨嘗試用各種渠道普及進食障礙的知識。“可在不被多數人重視的角落里”寫幾段話并沒有太多人關注,“有時候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她看來,卷入進食障礙的不少患者,都是從網絡上獲取了錯誤的減肥方法,以極端控制飲食的方式“一板一眼”地執行。
國家衛健委“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動”指導專家委員會運動專家組組長、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李可基指出,中國有4600萬成人“肥胖”,3億人“超重”。
這是個“以瘦為美”的時代,自拍軟件有“瘦臉”模式,纖細的模特和女明星爭奇斗艷,流行的“心靈雞湯”說,連身材都管理不好的人,沒辦法管理人生。
何一認為,“在一個把瘦與幸福簡單畫上等號的社會里,人們追求幸福的本能被粗暴地導向了變瘦。”
最初,北大六院主要聚焦藥物治療和病房治療,后來成立了進食障礙心理干預團隊,在病房或門診給患者疏導,也對家長提供培訓。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夠明白道理,一些家屬放棄咨詢,提起咨詢就暴跳如雷,“就像鴕鳥一樣把腦袋扎在沙子里”。
研究進食障礙10多年,李雪霓認為,厭食癥患者往往需要收治入院進行營養和行為治療。要醫好病,最難的不是更新治療方式,而是難以與患者搭建和維持一個“穩固的治療聯盟”。
在病房里,會出現各種狀況。多位醫護人員看護下,人們稍不留神,患者碗里的飯可能就沒了:要么抹得全身都是,要么扔滿床,或者丟到床底下,或者被猛地攥在手里。醫護人員伸手阻止,還可能會被咬傷。
很多患者都曾下決心戒斷極端的進食行為,但往往陷入一輪輪循環。李雪霓說,長期行為本身有神經塑形的作用,如果神經回路已被行為塑造好了,它就會變成習慣性的發生。其他可替代的行為要想發生,必須在足夠的動力和環境的配合下才有可能。“就是我們說的成癮性”。
何一形容,那是一種沖動來了“百爪撓心”的感覺,如果不執行,“整個人都要爆炸了”。
進食障礙患者中,多數人已經習慣“持久戰”。據李雪霓總結,患病大致分3個時間段,病程3年內是治療關鍵窗口期,痊愈率較高;3年到7年挺常見;7年再往上就麻煩了。
2015年,中華醫學會組織從事進食障礙臨床和研究工作的專家,共同撰寫了《中國進食障礙防治指南》,其中引證的研究稱,進食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約為5%。
“說進食障礙難治,是因為它沒有直接有效的藥,不是拿到方子就能痊愈。”李雪霓說,目前的治療方式,是按出現的一些癥狀吃藥,比如抗抑郁類藥物,或是根據局部性的損害做相應的治療。
陳偉接診的第一個進食障礙病人曾經“瘦到生命受到威脅”。營養科沒有病房,陳偉把她安排到消化科病房。他負責病人的一日三餐。因為病人的胃對固體食物難以消化,他們把食物打成了漿和汁。治療半年后,他收到對方的消息:體重漲到了120斤。
但是,很多人的體重都在上上下下。幾年里,北京的一位患者因為厭食癥從120斤跌到了79斤,又因貪食癥沖上了150斤。
“幫助他們康復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地發掘和維護康復的動力,反復是我們必須做好心理準備去迎接的。”李雪霓說。
用陳玨的話來說,進食障礙是一個譜系障礙,就像是一個“連續譜”,厭食和暴食分列兩端,病人落在了這條連續譜當中的某一個點上,可能暫時穩定,也可能一直搖擺,或者,沿著線往下走。
6
目前在中國,能為進食障礙患者提供專業化病房的醫院,主要有北大六院和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進食障礙診治中心。許多外地患者出院后很難在家鄉復診。
生活在美國,何一了解到,僅在波士頓,這樣的機構至少就有5家。
這兩年來,中華醫學會心身醫學分會進食障礙學組培訓了來自各地的醫護人員,有的學員回到當地后,開設了進食障礙門診。
但是,門診單一科室能做的很有限,要病房收治還需要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團隊,懂營養的、研究心理的,需要時間。李雪霓曾去英國的進食障礙中心參觀學習,她羨慕人家的治療團隊和硬件條件。她記得對方告訴她,是花了20年才變成這樣。“我想我們也是有希望的,也許用不了20年。”
北大六院的醫生已經明顯地感覺到,過去,患者要花3-5年才能找到癥結,但現在,這個時間被縮短為3個月到半年。
這些年,志愿者老曹看到,盡管醫護力量日臻成熟,還有為數不少的患者徘徊在社會的邊緣:有人消極不自救,有人接受了治療但還是無法恢復社會功能,讀不完高中。他們在與進食障礙的搏斗中,度過了青春期,邁入了成年。因為病情,只能應聘到一份工資低于自身能力或平均工資水平的工作,小心翼翼地生活。“就像把一個沉重的龜殼背在身上,他們卡在中間,如履薄冰地負重前行。”
程一喬和盧佳羽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們都成了北大六院的志愿者。盧佳羽和林樺決定把親身經歷分享出來,母女合著了一本書。沒想到的是,由于這次意外的“袒露”,她們成為這個群體里公開露面的冰山一角。
好消息是,盧佳羽不再對食物斤斤計較了。她體重升到了88斤。
(為保護患者隱私,文中患者及其家屬系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王景爍 來源:中國青年報
社會新聞精選:
- 2024年12月22日 19:28:23
- 2024年12月22日 18:26:01
- 2024年12月22日 17:05:36
- 2024年12月22日 16:58:29
- 2024年12月22日 16:51:33
- 2024年12月22日 13:38:29
- 2024年12月22日 12:19:32
- 2024年12月22日 10:11:46
- 2024年12月22日 09:21:13
- 2024年12月22日 09: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