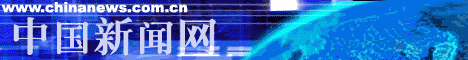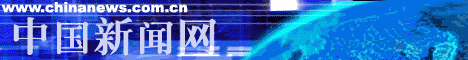酷:已經沒有人追究“酷”———“COOL”的淵源和變遷了,多數時候想都不想,也沒有一點感情色彩,張開嘴:“酷”———像白癡一樣。興奮地說酷,羨慕地說酷,都不如白癡一樣面無表情地說酷來得“酷”。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誰關心呢?一追意思就不酷了。難怪這個詞會泛濫,它跟這個目迷五色不知所云的時代太合拍了。
體健貌端:這是報紙征婚廣告生造出來的一個詞,全稱當為“身體健康,相貌端正”,大約是因為登征婚廣告要按字付費,所以字越少越劃算。這似乎代表了相當一批征婚者的心態:不一定漂亮,但也別歪嘴斜眼;不一定高大健美,但也別有慢性病。他們對婚姻的要求大抵也是如此,腳踏實地,量入為出。這也沒什么不對,但就不能表達得更有創意一點嗎?
策劃:好端端的一個詞就這么被毀了。大約是從點子大王何陽被質疑開始吧,策劃人從企業畢恭畢敬的大師淪為介于騙子和廢物之間的社會角色。市場嚴重不規范,企業乞憐于拍腦袋的“策劃”時期過去后,“策劃”這詞兒又被傳媒人接了過來,動不動“策劃”一本書,“策劃”一期專題,自我感覺還特別好,真明白市場、擅長策劃的人只好不做聲了。
工薪階層:這個詞呢,“工薪階層”自己倒不愛用,商家特愛用,通常打在裝修成本不高的餐館或卡拉OK的玻璃上,其實就是東西便宜的意思。但是,一個月掙多少錢算工薪階層呢?這個詞兒的流行和泛濫基本在北方,廣東人聰明多了,一律叫打工仔,打工仔也可以坐在五星級酒店里喝早茶,環境和觀念都不一樣。可以想像北京小餐館的老板,生意不好,沒招了,笨手笨腳地往窗戶上貼“工薪階層消費”的條子,憨憨地。
十大:魯迅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對“十大”病的諷刺曾使“十大”之說一度銷聲匿跡,可是這兩年“十大歌曲”“十大明星”“十大建筑”之類的評選越來越多了。這是一感性的活兒,不是理性的活兒,基本上沒法兒拿尺子量拿秤稱,所以全看功力。要是功力不到或者受其他因素左右,老百姓給這“十大”一大哄也是應該的。
閃亮登場:公關公司制作新聞稿,媒體拿來就用,于是便造成了“閃亮登場”的頻頻使用———無非是一個新產品出來了,得讓讀者兼消費者知道。一件衣服、一個須刀、一臺電腦,甭管閃不閃光有沒有腳,一律“閃亮登場”。
一族:這說法跟日本沾點邊吧?上班一族,SOHO一族,紋身一族……一族又一族。意思不過是這一群人,而且是外延模糊不清的一群人,加上“一族”就儼然時髦起來,就像小餐館掛上簾子取名“北海道”。
非常:鳳凰衛視購買臺灣娛樂節目《非常男女》播出時,“非常男女非常話題”還是一個有趣的說法。然而人們很快領略到“非常”從副詞變成形容詞的好處,就是可以不加節制地濫用,放之四海而皆準。這是一個包裝大于內容的時代,傳媒都在挖空心思搏出位,黔驢技窮之際紛紛抓住“非常”這根救命草,可見其“非常”貧乏。
另類:從前年開始,《格調》、《垃圾之歌》、《器具的進化》這類書挺暢銷的,可是名為“另類文叢”,就有點怪。“另類”在哪兒呢?也不怪編者,誰也不知道什么是另類、另類是什么;再說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今天的另類明天可能就變主流了,你敢揚起另類大旗,等于給人樹一靶子———找打。敢于宣稱“另類”的人還真不少,所以把“另類”這詞弄惡心了。
來源:中國文化報 作者:誠夫